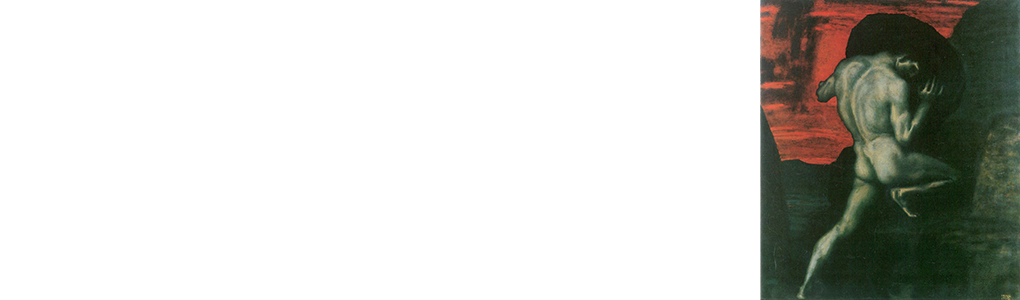每天,我都到复兴中路上的黑石公寓楼下喝咖啡。偶尔有朋友来,我会带他们到马路对面,去看音乐厅西侧围栏上的纪念牌子。每个牌子上,都有一个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家的头像和简介,其中有交响乐团创始人梅百器、音乐教育家萧友梅。乐团历史一百五十年,被纪念的人只有三十二个,然而在最右端,我看到六个名字 —— 他们依然健在,是当下的大腕。
我最想指给别人看的,是两个年轻的面庞:指挥家陆洪恩和钢琴家顾圣婴。
陆洪恩因反对样板戏,于1966年5月28日被逮捕,受尽折磨,1968年4月27日被枪决,终年四十九岁;顾圣婴则在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秦慎怡、弟弟顾握奇一同自杀,生命停止于二十九岁。
顾圣婴生于1937年7月2日,比我母亲大两岁。但每次看到她的照片,总觉得她只是个瘦弱、聪明、清清爽爽的孩子。这女孩是个罕见的音乐天才:十六岁开始登台与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肖邦,十九岁在莫斯科钢琴比赛获金奖,二十岁在日内瓦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最高奖,二十六岁在比利时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为表彰她对肖邦音乐的诗意诠释,波兰政府曾赠予她肖邦临终前的石膏手模。
顾圣婴活着的那个年代,上海还很小。她最熟悉的区域,如今成了最热门的城市旅游路线。人们浅薄地说这里小资,但我每天夜深人静在这附近散步,总觉得街巷充满悲情,空气里弥漫着无声的控诉。
从交响音乐厅沿复兴中路向东,左转进入汾阳路,就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校园里有几座旧别墅,曾是三四十年代上海金融大班的豪宅、欧洲诸国的领事馆,以及上海的犹太人总会。顾圣婴十七岁被上海交响乐团录用担任独奏演员,同时也在音乐学院接受专业训练,师从杨嘉仁、李嘉禄、马融顺、沈知白等名家。
顾圣婴死前,音乐学院和交响乐团已有数人被捕或自杀。当年三百多人的学院,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达十七人。如今公开资料中能找到的自杀者名字,只有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和夫人程卓如(音乐学院附中首任校长)、钢琴系主任李翠贞、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据说,上海音乐学院自杀人数之多,曾令来此串联的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感到沮丧:“我们那边怎么没人自杀呢?”
幸存的音乐学院教授李嘉禄回忆:“顾圣婴自杀的那天下午,我在淮海路上远远看到她在马路那一侧低头缓缓走来,步履沉重…我心里一怔,很想走过去问她一声,但一转念,当时自己也得随时汇报,圣婴处境也许和我一样,因此踌躇了好一会儿,终究没有走过去。”
李嘉禄见到顾圣婴的地方,离湖南路105号乐团排练场很近。就在那个下午,顾圣婴被揪住头发,拉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乐团全体人员的面,她被强迫跪在领袖像前“请罪”。一个“壮汉”上去打她耳光,有人踢她,也有人把痰盂扣到她的头上。
我曾从湖南路105号,她被批斗的地方,步行到愚园路1088弄宏业花园103号顾圣婴的家。这是她最熟悉的路径,也极可能是她人生最后一天走过的路。
顾圣婴回家经过的第一个路口,是武康路。如今这里和外滩一样,深受年轻人和外地游客追捧。附近很多大房子,五十年代从资本家和外国大班那里没收充公后,被分配给“进步”的文艺界人士。赵丹、郑君里分到湖南路洋房,巴金、王元化分到武康路别墅, 柯灵、俞振飞、张乐平分到五原路别墅, 夏衍分到乌鲁木齐路别墅,傅雷分到江苏路别墅,孙道临、王文娟、吴茵、王人美分到淮海路口的武康大楼。当时他们都曾对“新社会”感恩涕零,积极投入“新生活”,只是好景不长:有人在1955年就被打成“胡风分子”,其余几乎都没躲过1966年。
运动初期,自杀者多选择煤气或上吊。四十年代,公共租界当局在杨树浦建起煤气厂,上海成为中国最早普及煤气的城市。杨嘉仁、程卓如夫妇开了煤气,李翠贞开了煤气,傅雷夫妇在上吊前也打开了煤气阀。他们走得还算“从容”:李翠贞用旧报纸仔细塞满门缝;傅雷夫妇怕蹬倒凳子惊动保姆,预先在地板上铺了被褥。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却将自己欠缴的煤气费、水电费、房租安排妥当,如同苏格拉底临终前嘱托学生归还欠人的一只鸡。
到了1968年,自杀者可能已失去了使用煤气的“待遇”,更在无休止的折磨中丧失了最后的从容与尊严。于是,许多人选择了纵身一跳。沈知白跳楼,陈又新跳楼,上官云珠也是跳楼。跳楼不便的,则选择跳湖、跳河、跳井。武康大楼作为周边最高的建筑,楼顶有阳台,成为文艺界人士跳楼的首选。据考证,他们并没有跳向大楼两面的淮海路或武康路,而是带着绝望,坠入大楼中间那个孩子们玩耍的天井里。
穿过武康路口,顾圣婴应该沿湖南路继续向西,右转进入兴国路。她肯定不会知道,左边的兴国宾馆,此时正是她不能理解的殉地风暴的指挥中心。她更不会想到,兴国宾馆对面的民宅,十年后成了她父亲的新家,其中一个房间,成了她的纪念室。
兴国宾馆里有多座花园别墅,曾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们的住宅。被没收改为兴国招待所之后,下榻过多位国家最高领导人。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期间,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在这里“办公”,酝酿、策划对“牛鬼蛇神”的横扫。
兴国宾馆对面的兴国路41弄,是一片老式的居民小区。1975年8月29日,顾圣婴父亲顾高地服刑二十年后,从青海的劳改农场回到上海愚园路宏业花园。本以为妻子、女儿和儿子还在等他,回来才知道他们早已死去多年。“有关方面”给他回复:“不通知你是为了有利于你的改造”。顾高地无法承受再住在原来的家里,几经辗转求人,被安排住在兴国路41弄2号楼。他用余生整理顾圣婴遗物,编成《我的女儿顾圣婴》书稿,至死未能出版。在家中小小的顾圣婴纪念室里,摆放着女儿的旧钢琴、旧相册、演出时戴过的项链、以及波兰政府赠予的肖邦手模 —— 只是那手模的两个手指,早已被造反派们敲掉了。
兴国路的北端连着华山路。右边夏朵花园对面的海格园里,曾有梅兰芳女弟子、京剧和昆曲名家言慧珠的别墅。1966年9月11日夜里,言慧珠用演出时的白绫,在自家的卫生间里上吊身亡。“红八月”的血雨腥风从北方飘到上海,“自绝于人民”的高潮开始:傅雷夫妇死于9月3日,杨嘉仁夫妇死于9月6日,李翠贞死于9月9日。
现在终于轮到了顾圣婴。1967年1月31日,所有报纸都头版刊登了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加黑的字体现出杀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对反革命家伙坚决实行专政。
此时,离农历除夕还有八天,城市里没有任何节日气氛 —— 两天前已有全国通知:“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1967年春节不放假”。顾圣婴独自踉跄走过冬夜的街道,路灯昏黄,四周一片死寂。凛冽的寒风卷起地上凌乱的白纸 —— 那是被撕碎的大字报碎片,上面画着血淋淋的红叉,划过她可能并不陌生的名字。
走到华山路向左转,很快就到了江苏路。从宏业花园的后门回家,顾圣婴会经过安定坊5号傅雷的家。父亲顾高地与傅雷交情甚笃,童年时顾圣婴经常来这里,和傅聪一起学琴,聆听傅雷讲授文学。和她相比,傅聪天资略逊,为此常遭傅雷责骂。几个月前,傅雷夫妇在家门口被勒令站在高凳上接受批斗,当晚,夫妻便共同自尽。
江苏路的东侧,是顾圣婴的母校中西女中,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1881年创办,培养过宋氏三姐妹、张爱玲等名人。1952年,学校更名为市三女中。顾圣婴在这里从附小读到中学,是全校闻名的“钢琴神童”。借学校推荐,她十六岁就和上海交响乐团同台演出,中学毕业即加入乐团,成为职业音乐家。
沿着熟悉的路,顾圣婴回到宏业花园103号的家中。她在乌鲁木齐路的华山医院出生,小时候住过愚园路歧山村,也住过长宁路上的兆丰别墅。12年前父亲被抓后,兆丰别墅的房子被居委会收用,她和母亲搬到宏业花园103号外婆家的房子。这是一个连体别墅,共有三层。顾圣婴家住在一楼,楼上住着她的亲戚,包括舅舅和姨妈。
父亲顾高地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少将秘书。早年因对当局不满,顾高地帮助过上海地下党,与潘汉年、扬帆有过交集。他很早就已辞官,倾心培养拥有非凡天赋的女儿。不料潘汉年和扬帆被打成叛徒,而他则被无辜牵连。1955年,顾高地从家中被抓走。当时女儿只有十八岁,距一场重要的钢琴大赛仅有四天。那天被抓之后,顾高地再没见过家人。
在顾圣婴留下的日记里,话题几乎总是围绕着钢琴以及与钢琴相关的人和事。即便是在写给师友的信件里,对父母和弟弟也几乎只字未提。从亲友回忆和记录中看到,她没有谈过恋爱,生命中似乎只有钢琴。十几年中,父亲入狱、母亲患病、弟弟失业,但她至少还能演出,还能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然而现在,她自己也大难当头。
她已很久不能再演奏肖邦、李斯特和德彪西。在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里,她进工厂、下农村,不辞辛劳,诚心诚意地追求“进步”、接受锻炼。每次演出后,她都会记录曲目和钢琴品牌,并剖析自己的状态。
1965年7月26日,顾圣婴在国营118厂演出,曲目是《洪湖赤卫队幻想曲》,加奏《解放区的天》、《接过雷锋的枪》,使用的钢琴品牌是Moutrie。她还在手记中写道:“一月余未弹琴,昨日稍加练习,今日手指还算听话,唯精神疲劳,有些紧张,《洪湖》后部差点出岔。听众是热情的,但我感抱歉,质量不高,以后该怎样保证?不知!”
我手头有两本纪念顾圣婴的书:昔日同学周广仁女士主编的《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音乐评论家曹利群先生编著的《缺失的档案:顾圣婴读本》。两本书中,都收录了顾圣婴日记、书信和演出手记。其中,演出手记终止于1965年10月6日。那是个星期三,她在上海重型机器厂演出,曲目包括:《翻身的日子》、《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加奏曲目:《洪湖水浪打浪》、《采茶扑蝶》、《解放区的天》、《快乐的啰嗦》、《高举革命大旗》。
最后她写道:“目前这些作品基本上是熟练的,但质量上的加工、艺术处理上的熟虑欠缺了些,这需要练习的时间,总想学些新的,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
此时离她最终被打倒还有十几个月,而她的手记越来越短,很多次的结尾都是在焦灼地自问:弹什么曲目呢?何时能练琴?时间何在?是否不过硬,没有拼的精神?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没人知道,那晚顾圣婴被批斗后回到家中,和母亲、弟弟谈了什么,他们如何决定一同离世。1967年2月1日凌晨,顾圣婴的小姨从楼上下来,发现一楼房门紧闭,煤气味浓烈。惊恐之下,她破门而入,发现顾圣婴、母亲秦慎怡和弟弟顾握奇已昏迷不醒。救护车将他们送往愚园路748弄的长宁区中心医院,顾圣婴和母亲已经死亡,弟弟打过强心针,也没能救活。很快,公安局到家里查看现场,吩咐家人严密封锁消息,对外口径是三人死于不慎使用煤气中毒。

原上海交响乐团排练场
再过几天就是7月2日,顾圣婴的生日。为此,我又重走了一遍前面提到的路线。从淮海路转到湖南路,离105号很近的地方,有个小小的书店咖啡,门侧闪亮着中英文:我无比贪婪,我想要的是生命中的一切。
交响乐团早已搬到复兴中路,但湖南路105号那幢三层小楼还在。和附近很多大宅一样,厚厚的高墙上扎了篱笆,似乎要遮掩住一切。黑色的大门紧闭着,彰显着威严和神秘。它的主人是一家国企,拥有上海黄金地段昔日豪宅改成的酒店:兴国、瑞金、虹桥、西郊、东湖、太原别墅等等。
正是梅雨季节,城市阴湿闷热。我走走停停,来到宏业花园。从江苏路82弄进来,要经过一段破旧的街道,两边是杂乱的店铺。从愚园路1088弄出去,则要经过一段时尚市集。宏业花园被划为“优秀历史建筑”,门口牌子上介绍说:建于清光绪年间(约1900年),开发商是军阀段祺瑞之子段宏业。
宏业花园很大,中心部位是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院落。这里离顾圣婴家的103号不远,整个院墙用来纪念顾圣婴,有她的生平、彩色画像、以及大段莫名其妙的五线谱。这些都太粗糙了,更像是上个世纪的广告画。邻里们每天从此经过,可能从来都没想过:当年顾圣婴一家三口死了,骨灰都没留下来。
从此地向东八百米,我走到愚园路749弄。城市旅游指南介绍,这个弄堂里住过很多“名人”,如黄炎培、余日章、周佛海、李士群、吴三宝。我到这里,是想看看顾圣婴最后停尸的地方。
当年的长宁区中心医院,如今改成了妇幼保健院。在这里短暂停留之后,顾圣婴和母亲、弟弟的尸体被移至龙华殡仪馆,让亲戚们匆匆看了一眼,拉去火化。火葬费每人二十八元,相当于技术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也许是因为没人愿意承担八十四元的火葬费,也许是因为自绝于人民,不允许保留骨灰。总之,十几年后,顾高地寻遍上海,也没能找到妻子和儿女的骨灰。“组织”上应顾高地要求,为她举行过骨灰安放仪式,但仪式上的骨灰盒里是空的。
顾圣婴死去一年多之后,她的同事陆洪恩被判处死刑。执行前夜,陆洪恩嘱托狱友:若将来有机会出国,请务必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去年7月2日,顾圣婴生日那天,我曾将一小束鲜花,系在她纪念牌的铁栏上。当时我想,还要从宏业花园顾圣婴旧居门前捡一撮泥土,将来带到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洒在肖邦的墓碑前。
这次重访宏业花园,我放弃了这个打算。如果今后去巴黎,还是替她向肖邦献花吧。顾圣婴的灵魂太干净了,她实在不属于这里的泥土。
2025.6.30
后记:为纪念顾圣婴生忌,此文曾于2025年7月2日首刊于Boston Review of Books。在此特别要感谢罗小虎的修改意见,同时也要向罗小虎和读者们道歉,因为原文有个错误:复兴西路上共有32块纪念牌,而不是24块。其中,6块(而不是3块)牌子上的人还健在。

顾圣婴故居

2025年7月2日夜

2025年7月3日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