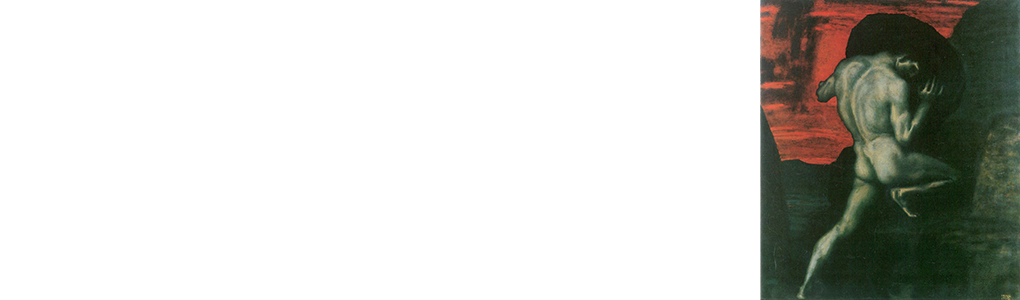春天来了,我搬了家。女儿曾在这附近读过小学,那时每次来接她,我都会提前过来,停车后在周围街道上转悠。没想过,十几年后,我会住到这里来。
当年的酒吧饭馆,几乎都已消失。贝尼还开着,窗户上用街头烤串店里常见的灯管,拼出“Since 1995”几个字。走进去,扑面而来一股久违的味道。可我已经不喜欢这个味道了,于是在服务生略带诧异和鄙视的目光中,赶紧逃开。高安路上的伊丽包子铺也还在,我买了两个,一个萝卜丝,一个梅干菜。所有的包子,都是两块五,只是比以前小了很多。站在路边几口吃掉,噎得我直打嗝。
开店可不是容易的事。租约时间短,房东也都不怎么厚道。生意好的话,到期给你提高房租;城市改造,更是容不得商量。以前家住古北,古羊路上一条街的店,一夜之间全部被拆光。孩子们小时候的记忆,也一下子就被粗暴地抹去了。
刘苏里在北京开万圣书园,三十年里换了五个地方。老任在上海开JZ,二十年搬家四次。我以前常去复兴西路四十六号的老店,如今房子还在,但已经被圈在了墙内。原来的门也被封上,没留下任何痕迹。从那里路过,无法想象这里曾是沪上爵士乐圣地般的存在。
离开复兴西路之后,JZ搬到巨鹿路的大同坊。店内正对着舞台,隔层曾经有个大包厢。这是老任的得意之作,也是他招待朋友的地方。开业不久,JZ被消防盯上,勒令整改。隔层被封,老任自己都不愿再来。此后,那周围陆续开了很多家酒吧,每家都电音轰鸣,都想在声势上盖过隔壁的店。走过那个小广场去JZ,就像穿越地狱,恐怖至极。有这样的前戏,让人完全不会再有听爵士的兴致。
大同坊不值得留恋,老任说,开业第一天就想搬。八年之后,他们终于搬到了衡山路。那是一百年前美童学校的旧址,马路对面,是当时美国人在上海的的社区礼拜堂。新店很大,更像个剧场。开业前晚,老任检查最后的布置,巨大的空间只剩下他、啤大和我三个人。“还挺紧张的,带烟了吗?”老任问我,然后想起他自己有两条大中华。“这是老查送的。其实他不送,我也会让他在这卖烟的。”
从汾阳路到复兴西路、巨鹿路,二十年里,老查每晚都在JZ门口摆摊卖烟。两个盒子里摆放的,一直也都是我没抽过的外国牌子。衡山路新店开业那晚,我在门口见到老查,第一次问他是哪里人。“我五湖滴。”“芜湖吗?我去过你们那里的查济村。”他眼睛一亮:“你去过?我就扎字滴。”“你们村可太有名了,我去过的。金庸老家也是你们查济村啊!”老查听了很得意,让我随便拿烟。
老任知道我住在新店旁边,建议我白天在店里写字,晚上待客。我看了一下新酒单,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些年里,白天我常去的,是那种很安静的咖啡馆。凡是我喜欢的咖啡馆,开不了几年就会倒闭。就这样,二十年里,我已经换过很多家咖啡馆。近来喜欢上晒太阳,发现能晒太阳的店,才能一直开下去。
安福路上有家Alimentari,最适合晒太阳。四年前疫情刚开始,全上海的咖啡馆几乎都关门,这里仍然开业。很多老外坐在那里,不戴口罩,阳光下满脸茫然。我和来自伊犁的伊璐在那里吃午饭,她说上海呆下下去了,她要去冈比亚给温州人当翻译。之后不久,伊璐便去了冈比亚,后来又借道塞内加尔,辗转到了法国。昨天看她发了视频,正用英文朗诵自己的诗歌,旁边有个姑娘伴舞,看上去很像嗑多了药。
上海所有街道中,我最熟悉的曾经就是安福路。两年前的春天,被关在家里很久,放开后立即骑车去那里,开瓶啤酒纪念解封。安福路193号开过一家意大利餐厅,名叫Settebello。穿过前厅,后面有个绿草萋萋的小院。如今,Settebello早已关门,除了费非和桃子,和我在那里吃过饭的人,几乎都离开了上海。
我没问过桃子的真名,叫她桃子是因为她住在桃江路上。现在成了邻居,她请我去吃街角的法国薄饼。这家店开了快二十年,桃子是熟客。自从和弹贝斯的毛里求斯男朋友分手,她的情绪一直有些低落。我委婉地劝她,这个年纪,以后不要再找老外了。她冷笑一声:中国男人谁会要我?桃子在Bumble和Tinder上都有注册,据她说,上海只剩下些教英语的老外,又穷又懒又坏。
黑石公寓在复兴西路上,里面有家Drops咖啡馆,是我新发现的晒太阳的好地方。前几天和汤小姐在那里喝咖啡,周围有几桌老外。提起桃子说过的话,汤小姐表示高度赞同:在上海超过一年的外国男人,都不值得交往。我很想说,外国人到中国会变坏,是改革开放后的现象。一百年前并不是这样子。而且,即使当今也有例外。我认识的外国人中,意大利人Erik就很可靠。他在上海近二十年,娶了徐州姑娘,有个可爱的女儿。Erik喜欢做饭,他做的佛卡恰和各种甜品无与伦比。桃子说,有手艺的人多半不至于太坏,她过去只找有手艺的男人。可惜,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费非和桃子都是上海人,我用双脚走出的对上海的熟悉,已经越来越让他们服气。相对于在公园散步或走进大自然,我更喜欢走街串巷。但我厌恶那些现代高楼大厦的街区,因为那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此外,那些似乎高贵但其实俗气无比的名字,消灭了所有可能的浪漫和想象力。国内所有城市中,大概也只有上海,留存着值得走的旧街道和小弄堂,掩藏着只属于上海的故事。这些故事令人痴迷,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奇迹与磨难、聚散与悲欢。
张珑是民国出版家张元济的孙女,早年生活在上海,毕业于中西女中。我读她的回忆录《水流云在》,很感兴趣其中关于旧上海的记忆。她写过静安寺路(南京西路)上的沙利文西餐馆,西摩路(陕西南路)上的富特勒食品店,以及善钟路(常熟路)上的上方花园。上海的故事,总和某条街、某座房子、某家店有关。店消失了,如果地方还在,回忆便依然能生动。因故事而被记住,对于开店的人来说,既是慰籍,也是激励。
几场春雨之后,天气越来越暖。很快,住处附近的街道,都会被梧桐树的枝叶覆盖。这些梧桐树已经栽下了近百年,两侧的房子也早已换了主人。我无法走进、甚至看不到高墙背后的宅邸,但我知道,在那里,阴谋取代了轻歌细语。这里还有很多弥漫着烟火气的弄堂,那些曾经精致的洋房,被若干人家挤住着,袒胸露怀,疲惫不堪。外墙风化了,油漆褪色了,楼梯倾斜了,只有裂缝和角落里,藏着往昔。我很想去贴近看个究竟,让那些不该消失的,不被忘记。
2023.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