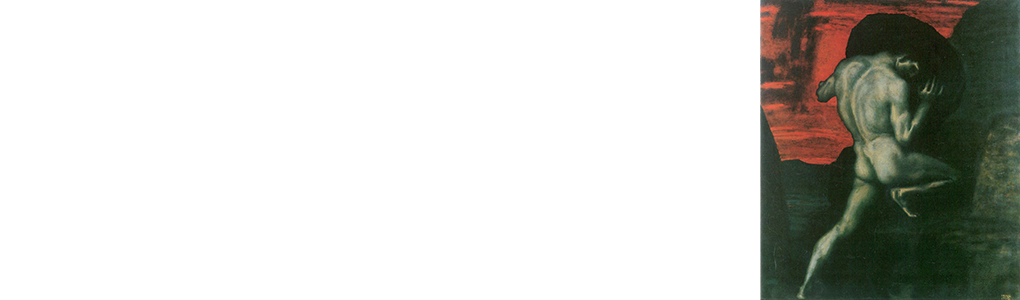深夜才到香港,照常住湾仔的酒店,放下行李就去吃潮兴鱼蛋粉。走在街上,脸上瞬间就湿漉漉的。这样的雨,比英国人讲的pissing rain还要细很多。心情极其糟糕,这与天气无关,与那个日子更无关。我骂自己,真没出息。
第二天醒来,打开朋友圈,看到小本发了一张蜡烛的照片。小本在纽约做律师,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他发什么我都点赞,他也会给我点赞。我转发了他的蜡烛照片,不过很快自己又删了。何必呢,自己记着就行了。
这次来香港办事,只花了半个小时。结束后去了时代广场,帮人买个Gucci包。服务员是个像男孩的当地女孩,自我介绍名叫Ashley,英语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标签上要刻字,她要求加我的微信,弄好后通知我过来取。刚在楼下喝完半杯咖啡,Ashley就发来消息:哥,可以来取了。
在上海找福建人阿琪理发,已经十来年。他爸爸比我还小,但他总是管叫我哥。店里做按摩的女孩叫夏夏,来自安徽,刚满二十岁,却也管我叫哥。我建议过几次,还是叫叔合适。但说了也是白说,他们还是哥啊哥地叫。哥就哥吧,铜锣湾也都哥了。
从时代广场走回湾仔,路上买了信报、星岛日报、经济日报、明报和南华早报。轮椅上有个男人捅我屁股,原来不小心我有几张钞票掉在了地上。卖报的老女人呱啦呱啦说话,我听不懂,连连鞠躬致谢。回到酒店房间,只用半个小时就把一摞报纸翻完了,扔到垃圾桶里,居然装不下。
天气预报说有雨。天的确是阴的,风很大,雨却并没有下。维园每年这几天都要搞嘉年华,电视里说有很多警力维持秩序,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人去。我脑子里反反复复,总是绿洲乐队在Wonderwall里的那句歌词: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今天将是那个日子,他们会将它抛回给你。
钟浩是我毕业后在研究所的同事,在香港两天里,我只想和他见面。三十五年前的春天,我从北京到香港,停留几天后去伦敦,而钟浩此时已在香港学习。我有那天的合影,虽说西装领带,其实我们是去看了小电影。前段时间钟浩说,那个电影院也关门了,不少当地还人去拍照留念。
这次见面,我们又拍了一张合影,算是个纪念。本来想和旧照一起,发到朋友圈里,但对比实在太不堪,于是发给了女儿,告诉她这是时隔三十五年。她回复,哇哦。
这些年里,钟浩一直在香港,做些和金融有关的事。我们本来只是约在交易广场的翠玉轩吃饭,最后餐厅只剩下我们俩,于是便跑去坚尼地城的酒吧;酒吧打烊,又打车到湾仔的潮兴鱼蛋粉吃宵夜。六个小时里,工作上的那些事几乎没提。回忆起少年时读的书,大学时代的文学梦想,以及进研究所的故事,才发现这辈子值得自豪的经历,居然发生在二十来岁。那时我们对如今人们热衷的事情全无感觉,对未知和未来充满好奇。
香港不是他乡,而曾是最近的远方。在这里与故知相见,真开心仍有孩童般的亲密。提起过去这三十五年,难免心有戚戚。幸运的是,我们没想着去改变这个世界,也因少年时吸进内心的那点光亮,还不至于完全被世界所改变。成败与得失并不值得计较,难得这般年纪还想讨论人生的意义,还能互相勉励。太多耽误了的年华,太多难以清除的毒害,太多走错路的懊悔,都不必去唏嘘,更重要是对未来仍有期许。有些缺憾永远无法弥补,阴霾密布看不清时势的轨迹,我们都想赶紧放下眼前的琐碎,重新找回昔日的好奇。至于年轻时朋友们共同的愿望,也许此生都无法实现,但世界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希望是个好东西,也许是最好的东西。好东西就应该留着,不需要十年,三五年就能见分晓了。
夜已深,风继续吹。儿子放暑假,从伦敦飞回来,再过几个小时就落地上海。我回到房间,又听了一遍Wonderwall。Noel Gallagher 说,他这首歌是写给一个想像中的朋友,能把他从他自己那里拯救出来。谁能拯救我呢?这个问题很难,但我已接近知道答案。其实,摇滚歌手填词,未必知道自己想讲什么,有时只是文字游戏;对于听者而言,却总有几句,应和着某一刻的思绪。
今天将是那个日子,他们会将它抛回给你
现在你应该已经知道,你必须做的事
我不相信还有人,像我此刻这样感受你
街头正在传言,你内心的火焰已经熄灭
相信你早已听说,但从没有怀疑自己
我不相信还有人,像我此刻这样感受你
我们要走的路曲折盘旋
引导我们前行的灯火炫目耀眼
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但却无从说起
因为也许,只有你能拯救我
而且终归,你是我的神奇的墙壁
今天本该是那个日子,但他们永远不会将它抛回给你
到现在你应该已经知道,你不应做的事
我不相信还有人,像我现在这样感受你
带你去那里的路曲折盘旋
照亮前方的灯火炫目耀眼
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但我却无从说起
我说也许,只有你能拯救我
而且终归,你是我的神奇的墙壁
202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