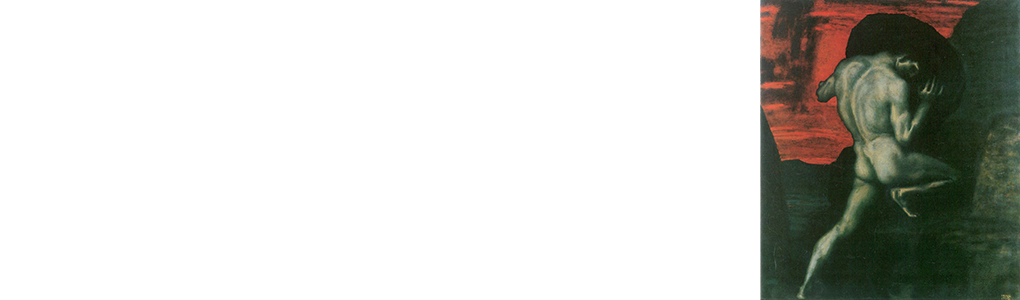每当回首往事,想起浪费了多少时光,想起为徒劳、错误、懒惰、无力生活消耗了多少岁月,想起有多么不珍惜生命,想起多少次对自己的内心和灵魂犯罪…我的心就会流血。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

保罗说话的语气,就像我们还常见面。“你来塔桥吧!泰晤士河边停着那艘皇家贝尔法斯特号,咱们在门口见,你不会错过的。”
离开伦敦已经二十七年了,中间回来过几次,和保罗上次见,还是十三年前。不过,我依然熟悉这里。从西北的帕丁顿到东南的塔桥,差不多十公里,我要走路过去,中间好几个地方要看看。
约好五点半见面,一大早我就出发了。“网友”吕枫从洛杉矶过来,在哥文花园的常春藤餐厅和闺蜜吃午饭,顺便约我首次见面。我看了下她下榻的酒店,一万多人民币一晚,有钱人!中午肯定不用我买单。
穿过Marble Arch、Oxford Street、Mayfair、Chinatown。经过一座天主教堂,进去休息了半个小时;路过Soho,在马克思故居对面的咖啡馆喝了杯奶茶。这个城市高冷又亲切,我想起《加州旅馆》最后一句歌词: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of the night,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伦敦于我也是如此:随时都可以走人,但永远无法离开。
曾经去过路过的酒吧还在,它们已在同个地方开了几百年;唐人街还是以前的样子,龙凤超市已开门迎客,对面茶餐厅的橱窗里挂满新出炉的烧味;Shaftesbury Avenue上,《悲惨世界》还在上演,从1985年到现在,同样的剧照,美丽瘦弱的女孩;路上匆匆的行人,男的,女的,不男不女的,也都和当年一样。一切如旧,只有我不再年轻。回故乡应该就是这种感觉的,不过回我的沧州老家就没这种感觉。
午后艳阳高照,伦敦街景如天堂般绚丽。我带女士们在剧院区闲逛,不知不觉中走到伦敦经济学院。小小的Wright’s Bar还在,某个夏天门口短暂竖起过白色女神塑像,我在旁边Old Building的台阶上拍过毕业照。拐角那里的老古玩店,是狄更斯小说的原型,如今重新刷过新漆。不知接下来他们是否还会将当年的店名写上去:Old Curiosity Shop,Since 1573, Immortolised by Charles Dickens。新加坡的同学凯瑟琳曾经说,在这里开店卖肉骨茶多好。
那天带女士们游览的终点是不远处的圣殿教堂(Temple Church)。吕枫指给我看,不起眼的牌子上写着:从1163年起,伦敦的耶路撒冷;从1214年起,普通法的摇篮;从1584年起,美利坚在伦敦的教堂。
圣殿骑士团最初创立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作为十字军东征时朝圣者的护卫,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和影响力的武士社团。1163年开始,英格兰的圣殿骑士们在此聚会并建造教堂,圆柱形的中殿象征着与耶路撒冷圆顶圣墓之间的渊源;1214年,约翰王遭贵族们抗议,曾躲在这里受到骑士和教会的保护,多番角力博弈之后,不情愿地签下《大宪章》,从此也奠定了普通法的基础;1584年,清教徒们在这里曾与官方宗教势力展开论战,为了建立理想中的世界,他们从此启程,穿过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奔向了美利坚,而《大宪章》后来又影响了《独立宣言》。
所有这些,都是我那天参观教堂时才学到的。伦敦那些年,我曾无数次从Temple地铁站进出,但从来不知道有这个Temple Church。直到多年之后,读到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才知道这里是传奇圣迹。
从Temple地铁站到学校之间,每天也要经过属于皇家空军的圣克莱蒙教堂。我对吕枫说,撒切尔夫人举行国葬时,灵柩都曾停在这里,祈祷后由炮车载着,沿舰队街送到圣保罗大教堂。教堂门口有两座铜像,左边是“轰炸机”阿瑟-哈里斯(Athur Harris),右边是休-道丁(Hugh Dowding), 他们都曾在二战期间指挥过英吉利海峡的空战。女士们夸我是个好向导,但我觉很惭愧,因为以前只是路过,从没进去圣克莱蒙里面。
我经常问自己,年轻时为什么对身边的风景视而不见?为何对旅途中古老的遗迹毫不兴趣?为什么耐不住寂寞,将大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热闹上?
在伦敦七年多,我只去过一次大英博物馆,而且只看了很少几个展馆;无数次去唐人街买菜吃饭,但只匆匆去过一次旁边的国立美术馆;曾经住在Earl’s Court,却从来没走进过附近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在西敏寺大教堂里,Jacky细心给我介绍那些名人的墓穴,而我竟如梦游般无感;学校附近的剧院区,每天都上演着很多举世闻名的音乐剧,我一个都没看;杂志和报纸上每天都招募各种伦敦徒步游,我也从来没参与过。
那些被错过的地方还可以重游,那些古老的痕迹还可以再次寻觅,但有些人却永远找不到了。深夜难眠,脑中会掠过些旧日时光。有很多人,尽管和他们曾朝夕相处,尽管和他们曾呼朋唤友,尽管他们当中也不乏精英权贵,但他们于我没有任何追忆的意义。时光流逝,一些面孔却又无比清晰起来,从遥远的过去,笑眯眯地看着我。他们平凡、体面、充满善意,他们是我中年后才又想起、而终生将不愿忘记的人。
最初到英国,为省钱我找到一座破旧的大房子,住宿免费,条件是帮房东贴墙纸刷油漆。和我同住的,是来自约克郡的Gerry Riordan。他在建筑工地上做工,每周发工资都会带我去吃中餐,每次餐后他都偷偷独自再去吃个汉堡。第一次在国外过圣诞,Gerry给我买火车票去他老家,和他的家人一起吃火鸡餐。他只对我严厉过一次,因为他说闻到我身上有毒品的气味。还好,那是个误会。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也曾称呼别人为大哥,但对我来说,Gerry是此生唯一像哥哥的人。
我记起三十年前Jacky Jennings略带羞涩的笑容,她脸上的每条皱纹都洋溢着温暖。Jacky和我母亲应该同龄,在研究中心给Jean Dreze博士做秘书。在我最难过的日子里,她带我去西敏寺大教堂,走过无名烈士、牛顿和狄更斯的墓地,去附近圣詹姆斯公园的草地上午餐听演奏。她能讲很多历史故事,只是那时我太无知,甚至可能都没表示出听故事的兴趣。
曾经,Jacky是我理想中未来岳母的形象。当然,我从没奢望能娶到她的女儿。
进入公司工作后,最难忘的是送信员Frank。那时他应该有六十来岁,高挑的身材,爽朗热忱的声音,看气质和衣着更像是大学教授。的确,他很博学,加以不露锋芒的幽默和善解人意,一直是全公司最受欢迎的人。每天午饭后,女孩子们都围着他在公司楼下喝咖啡,听他讲笑话、向他咨询人生小问题。部门女秘书Els曾跟我说,她周末在大学里读哲学硕士,Frank还是她平时的指导老师。
因为同是单身,我和Frank一起度过若干周末。可是,我自己太浅薄,无法和他探讨有深度的问题,也没听他讲自己的故事。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此生可能错过了一个最好的老师,只是这时甚至已忘记了他的姓氏。
那天在塔桥见到保罗,高大的他给我一个熊抱,然后我们打量着对方的老相,忍俊不已。年轻时和保罗一起出差,晚饭后在酒店游泳,每当他从水下钻出来,甩起满头金发,就像一头英俊的雄狮。现在,他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而我的胡子都已全白。
路边坐下来吃饭,我迫不及待地地对保罗说:当年在欧洲出差,他曾抱怨为何每次都要由他租车开车。当时我给他的理由是因酒驾被抓,驾照被临时吊销。“保罗,我心里有个疙瘩,一直想亲口告诉你。其实我当时根本没驾照,面试的时候就撒谎了。我在英国考了六次才拿到驾照,实在没脸跟别人说,才编出酒驾被抓的理由。”保罗听罢哈哈大笑,说他早已不记得了。
之后,我们谈起Frank,谈起我们的老板迈克,谈起我们共同的令人窘迫的往事。保罗也讲了他自己的故事。
十七岁时,为了学德语,保罗去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小农场主家里过暑假。没呆多久,他就特别想家,原定的三个月没住满,就跑回英国。保罗说:“很多年后,我才想起来,那个暑假其实有多开心!每天都是蓝天白云,放牛、劈材、晒太阳、看书,无忧无虑,真是最美的一段日子。”
从那以后,已是中年的保罗每个圣诞节都会给那个农场主写信,告诉他自己的近况,寄上自己家人的照片,并感谢农场主全家多年前的热情招待。
我也想给Gerry、Jacky、Frank写信,可和他们已失去联系太久,这是我此生很难平复的深刻遗憾。
伦敦的春天还很冷,傍晚的阳光依然明媚。保罗建议我们沿着泰晤士河南岸,边走边聊。可我已经很累了,没走多远,就想停下来休息。保罗以为我身体不好,我对他说,那天我已经走了将近三万步。他很惊讶:“耶稣啊!你怎么会走这么多路?”
“因为我想仔细看看以前错过的地方。记得吗,咱们当年在欧洲出差,周末完全可以留下来。米兰、威尼斯、哥本哈根、马德里,都是好地方,公司报销所有费用,但我们都会飞回伦敦。你有女朋友还好,我是单身,回伦敦只是为了找熟人喝酒,讲老板坏话。现在想,迈克这家伙真不错!”
“对啊!我喜欢迈克的。那时出差真没啥事,大把时间,好吃好喝,我只想每个城市都找个女朋友,对别的完全没兴趣。”保罗现在绝对是个好男人,谈起他的西班牙太太和两个可爱的女儿,满脸幸福。
“我们当年错过的东西太多了!”
“是的,因为我们年轻而且愚蠢。”保罗说。
2023.6.13

和Gerry在唐人街,1989

Frank在家门口,1996

保罗在德国,1995

和保罗在泰晤士河南岸,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