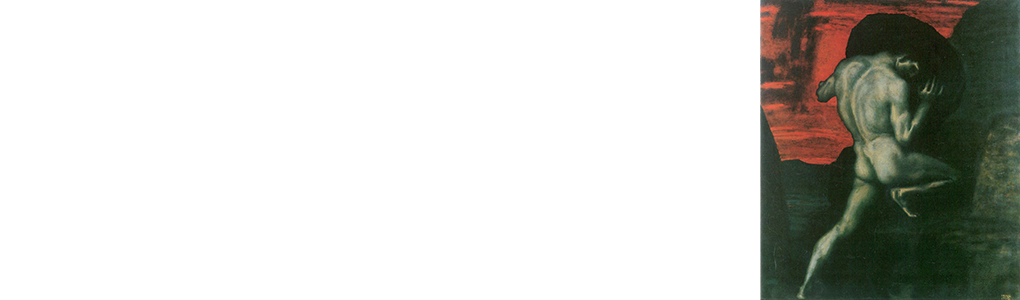去年六一下午,我独自坐在水城路BeerPLus外面喝啤酒。十几个小时之前,在小区门口,我郑重地从保安小张手里接过剪刀,于零点到来之际,剪断了那条红白两色的塑料带。这条薄薄的带子存在了整整两个月,曾是无法跨越的屏障,其坚固和庄严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深宅高墙。
我平生从没剪过彩,为获得这个难得的机会,还特意送给小张一包玉溪。虽然没有穿红色开衩旗袍的礼仪小姐捧剪刀,也没有任何邻居下来鼓掌,我仍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白天,看着步行街上的人们欢天喜地,我写了篇短文《愚人节和儿童节》。不过,发布之后,很快也就被删了。

今年儿童节,我再次发现,每人都长了一岁,童心却都似乎更加鲜活,一大早就有人奔走相告节日快乐。孩子们可能有半天放假的欢快,老男人和中年妇女的“顽童”梦想却整天都在放飞。
的确,对“小”的膜拜几乎具有了宗教般的响应。且不说小盆友小伙伴小哥哥小姐姐成为最受欢迎的称呼,所有的品牌似乎也都要带上“小”字才会有市场,如今购物,就像在逛迷你版的动物园。
顽童的吸引力不容忽视,金庸笔下的周伯通曾是无数人的偶像。其实,顽童代表着某种男权传统,就像老头子们的玩鸟,就像大老爷们挤在一起逗蟋蟀,就像几千年的酒桌文化。如今,顽童不再只是男人们的追求,夏日傍晚的城市广场,已被花枝招展的阿姨们占领。
顽不是玩,“顽”代表着一种拒绝,比如拒绝长大,比如把装疯卖傻当成童心未泯,比如把不堪的青春浪漫化,比如放声高歌做一只小小小小鸟儿。只是这种拒绝必须要以遗忘为前提,必须以群体的参与获得正义感和合理性。顽童的确是快乐的,他们只有节日,没有纪念日。
然而记着分明是有意义的,记着才能不再一代又一代,不再循环往复;记忆是成长的标志,记忆才能让过往的悲剧和牺牲更有意义。
不能记着的人不是成人,所谓的少年感无非就是孩子气,成年人的童心无非是痛感器官失灵,装嫩也多半是以浑然的方式掩饰愚蠢。从这个意义上说,顽童和巨婴没什么区别。
其实我并不喜欢巨婴这个说法,心理学上所说的“彼得潘综合症”可能更为准确。写下过《美丽新世界》的阿德斯-赫胥黎曾经警示,彼得潘综合症是心理变态,成年彼得潘的肆意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据说人口老龄化已是必然,照此看来,未来会不会满大街都是老顽童?那样的话,儿童节的确会更受欢迎。这样的场景细思恐极,所以,成年人与其呼喊“救救孩子”,真不如想办法救救自己、饶了孩子吧。
202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