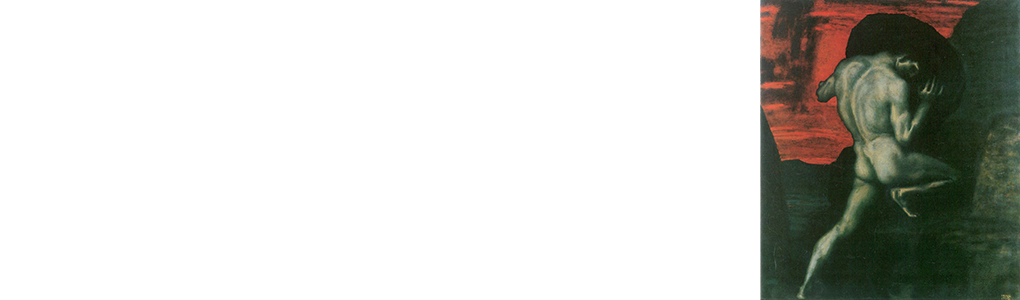世界在发烧,热得不成体统。我和戴安娜约好晚饭后去老外街喝一杯,聊聊人生意义等重要问题。为了找个清净的酒吧,我提前十几分钟到。没想到,周末之夜,每个酒吧都很清静,果然今非昔比。在上海,这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孩子小的时候,周末常约爱德华一家来这里吃饭。希腊餐厅的隔壁,曾经是荷兰人开的面包坊加餐厅。室外,有几排厚厚的木桌。阳光下,两家四个小孩子跑来跑去,逗喂着墙边笼子里的灰白两色的兔子和懒洋洋的流浪猫。整个下午,桌边人来人往,晃过无数不同颜色形状和光洁度的大腿。遮阳伞下,爱德华的太太琳达没有动面前的拿铁和蛋糕,两只漂亮的大眼睛一直捕捉着老公飘向人群的目光。“哇,那个女孩身材真好!”她经常这样感叹,我和爱德华赶紧转头,相视不语。
十几年过去,小孩子们都已长大,按预定计划去了国外。我很少再见到爱德华夫妇,偶尔听他提到琳达,总是咬牙切齿。老外街的冷落已非一朝一夕,说不定哪天也就和上海无数的旧时地标一样悄然消失,就像从来都没存在过。儿子小时,我常牵着他的手,去古羊路东南亚美食街吃吉亨的半筋半肉面。西侧伊犁路这边,夹杂在脏兮兮的出租司机饭馆中间,有几家美容店,不论冬夏,里面都会坐着几个穿短裙露大腿的姑娘。儿子问:“老爸,为什么那些阿姨都向你招手。”我说:“等你大了,阿姨也会向你招手的。”如今,儿子已成年,这里所有的铺面都已被推翻。昔日美容店聚集的地方,现在是十五号线的姚虹路地铁站。
八月的这个晚上,室外闷热如蒸笼。老外街临近虹梅路一端,有家名叫Fat Cow的美式汉堡,里面零散有几桌客人。于是,我发短信给戴安娜,约她来这里。别的地方都太过冷清,弥漫着霍普画里那种后现代式的诡异。坐下来之后,戴安娜告诉我,她很快就要去新加坡,做亚太区的负责人。真的要走吗?那么优秀,还需要证明什么?她微笑着说:不只是为了证明什么吧!文博士在爱尔兰做投资移民中介,最近生意再度火爆。真有人走吗?我感觉不灵敏,只是发现流浪猫的确多了起来。你们都太狠心了!
就在见戴安娜的那个周末的下午,仲伟约我告别,他要和女朋友去定居泰国。“好啊,我很早以前就向往退休之后去清迈。”其实我从来没去过泰国,对清迈的了解仅限于安东尼-波登的美食纪录片。
“噢,我们是去曼谷。不过清迈也不错,现在大理很多人都搬到清迈去了,野夫也去了那里。”仲伟一边说,一边打开他在曼谷的创业计划。那天我们约在1691酒吧,老板小殷在旁边插话:“野夫这老家伙,泡妞可是高手,真的有一套,在大理有不少女朋友。”说完野夫,又聊了几句张贤亮,清迈在我心中的映像越来越灰暗。
也许可以考虑马略卡!唐几何前些年去了西班牙,最早在巴塞罗那开中餐馆,后来因为竞争太激烈,于是跑去马略卡岛上开起了新疆烤肉店。他说:“马略卡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中国人很少,都是英国人德国人过来晒太阳,这里没有像样的中餐馆,露天烤肉才受欢迎。”唐几何是我的同乡老大哥,我从小就认识他,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以后再讲。
小殷的酒吧原来开在长乐路,三月份搬到恒隆广场后面的奉贤庭,刚装修好就遇上了上海两个多月的封控。解封之后,小殷将两个大包间改成了私房菜餐厅,只有每人六百和八百两个档次,不准点菜,据说预订很满。小殷热情地带我参观他的厨房和两个包间,我惭愧地想着未来应该不会吃这么贵的饭。很多年前,我给农民企业家打工,那时经常要出没各色会所,有时洗澡,有时喝酒,有时吃饭,有时洗澡带喝酒带吃饭,每位800元只够喝碗海参小米粥,属于请客的最低配版。那是多么不光彩的岁月啊!每当酒足饭饱在酒店洗手间的镜前看着自己隆起的肚子,我都想学《猜火车》上的麦克格里格那样将脑袋扎进马桶,然后摁下抽水的按键。
世界上最早写美食的作家是法国人萨瓦林,他有句名言:告诉我你吃什么,我能说出你是什么人(Tell me what you eat, and I will tell you who you are)。混迹多年之后,我可以把这句话改成:告诉我你在哪里吃,我能说出你想要什么(Tell me where you eat, and I will tell you what you want)。来酒吧吃八百一顿饭的人们想要什么呢?我看看四周,环绕舞台的是三面满满的书墙,穿短裤的胖子坐在凳上怀抱吉他深情地唱民谣,吧台对面墙上挂满了死去作家的黑白照片,店里每一片空白的地方都用英语写着名人名言。小殷在朋友圈经常发他在这里和漂亮姑娘的合影,但我来得不巧,每次遇到的大都是小屁股细腿大肚子的中年眼镜男。朋友于辉很喜欢这里,那天我带他过来,他一直用手机拍视频,转头对我感叹,唱得真好!真好!于辉以前最不喜欢民谣,十几年前我俩在北京混,他总带我去那些唱摇滚的Live House,现在统统改成了火锅店。
认识小殷让我彻底放弃了今生要开酒吧的梦想,像他那样记住那么多客人并保持春风满面,难度极高。他说要做上海最知名的只传播灵魂不卖肉体的文化妈咪,在为他点赞的同时,我很想提醒他:灵魂交易的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副作用可能远远要大于出卖肉体。小殷很受顾客欢迎,人们都夸他文艺、理想主义、桀骜不羁。我最喜欢他热情爽朗的笑声,其次他也是全中国留齐肩长发最好看的两个男人之一。另一个是我外甥,上海解封后便跑去了大理。至于其他那些把头发编起来支愣着翘在脑后的男人,看上去都像秦始皇兵马俑的后代,我常担心当他们解开小发髻的皮筋,里面会不会飞出几只白蚁。
以貌取人是现代社会化繁为简的生存之道,这不是偏见,只是偏好。小殷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对此我深表赞同。王尔德说过:选朋友要看其长相,选熟人要看其性格,选敌人要看其智商。我没有敌人,也不想与人为敌,在交往方面的选项只有两个标准:要么好看,要么好玩。
正是基于这个标准,前些天去北京,只见了很少几个人。在好运街潮汕牛肉店一个狭小的包间,我和学生时期最要好的几个伙伴吃饭。昔日志得意满的大老爷们儿现在都改喝北冰洋汽水和酸梅汁,翻来覆去聊的都是谁上谁下那些破事,骂骂咧咧中时光飞逝。在北京还有些体制内的同学同事,有几个被抓了,剩下的几个也都接近二线,据说开始主动拿出多年来收藏的茅台招呼老同学们凑局。和他们交流,我素来有心理障碍,不介意老死不相往来。每次来北京,我更愿意找认识多年的莫莫姑娘吃饭喝咖啡,她的出现让我相信在这美颜泛滥的世界上确实还存在天生丽质。几天前莫莫在朋友圈说:越好看的女人越瞎,越寒碜的男人越渣。我留言说这话让人反省,她回复说我不算寒碜。这也未必,按她的理论,是否寒碜要让不好看的人来判断,对此我了无兴致。
莫莫的感慨也让我想起这次在北京见到的梦洁。几年没见,她又长了两公分,身高到了一米八,牵着个长得完全不像她的上幼儿园中班的男孩。梦洁曾经是模特大赛的冠军,数年前从深圳嫁到北京。望着她瘦弱的身板和憔悴但依然动人的面容,听着她讲述婚姻生活中的不堪,莫莫的结论似乎再一次得到验证。不知是否属于巧合,凡跟我熟悉的人,不管男女,婚姻几乎都出了问题,有些早已了断,有些还在危机。总之,我似乎极少遇到感情生活幸福美满的人,互相或者在骗别人,或者在骗自己,或者两者都骗。于辉和梦洁都是多年的朋友,会跟我讲述他们的烦恼,但除了动员他们赶紧离婚,我想不出别的解决方案。所幸的是,叹气之后,他们都不会接受我的建议。让人们仍在一起煎熬的并不是孩子,就像粉碎爱情的绝非柴米油盐,在所有冷漠、焦虑、争吵、纠缠、互相憎恨和欺骗的背后,既没有新意,也没有美感,表面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其实没啥事和钱真正有关。
那晚在丽兹卡尔顿楼下送走梦洁和她的儿子,我打电话给只在白天睡觉的南风。他说北京现在找不到酒吧喝酒,于是我们约到酒仙桥附近最早的漫咖啡,那里至少还能坐到十二点。我来回打出租车掠过那些熟悉的地方,一路黑灯瞎火,一路闭口无言。北京司机的所谓洒脱和幽默都只是传说,真正经得起岁月的只有空调也吸不掉的大蒜味道,这让我想起金汇路丰盛胡同的卤煮火烧。这里的夜晚已经凉爽宜人,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傍晚的时候,我首次在首都以性感且不失体面的姿势做了核酸,明天回上海,那里未来两周依然每天四十度。高温不可怕,值得记忆的事情都发生在酷热的日子里。蒸笼岁月,不能大声说话,不妨大口喘息。
2022.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