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自幼胆小怕事,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直是最瘦小的那个,总是坐在第一排。在农村,瘦弱意味着第一不能干活,第二不能打架,不仅会被嘲笑,还要受欺负。
因为打不过任何人,我很小就学会了逃跑,远离那些强壮的孩子。但凡遇到威胁,第一时间跑掉。想跑又跑不快,难免有时会挨个三拳两脚。但一般情况下,胜利者只是希望看到你害怕,逃跑证明你已经怕了,他们在你身后大笑,并不一定追赶你。
每次受气、逃跑,我都会感到很屈辱、很难过,经常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梦想某一天能练就一身武功,回来报复那些欺负我的人。但真的长大之后,就忘记了这些昔日的誓言,我记不起曾经被哪些人追打,也不关心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成了与我无关的人。
童年的弱小,让我早早地就放弃了英雄梦,但也培育了随时准备开溜的本能。如今,蓦然回首,竟发现我生命中的许多事件,总与逃离有关。逃离过去,逃离人群,逃离暴力,逃离感动,逃离现场,逃离温情。
逃,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宿命。我逃,故我在。
2 1
考上大学的时候,我15岁,身高1米56,体重42公斤。班上同学基本都来自城市,年龄大一些,个子高出很多。我瘦小土气,一无所长,非常自卑,不怎么敢找别人玩。此外,我对工科的课程没有任何兴趣,成绩也不好,课外大部分时间躲在图书馆读外国小说,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充满与我年龄不相称的好奇。
好奇也没用。我们理工科学校女生很少,别的男生又很高大,体育也好,像我这样的,没有任何机会,幼小的心灵充满挫败感。
少年维特式的烦恼其实算不了什么,真正让我压抑的,是学校里那种沉闷、世故的气氛。我看不懂,小小年纪怎么可以做到那么老成,拍马屁、玩政治,样样精通。那个年代,毕业要统一分配,和辅导员、班主任、系里书记的关系可能会决定人生。我一边读着莫泊桑、卢梭、大仲马,一边眼看着周围同学的积极表现,无所适从。我不知道该如何追求进步,如何向组织靠拢,而辅导员打量我时那浑浊和不屑的眼光更让我胆战心惊。
几乎所有人都会怀念大学时光,都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而我完全没有。我不喜欢那里的任何一门课,也从没敬仰过任何一位老师。但我把所有的迷惑和不适都看作是自己的过错,对可能被分配到边远地区工厂的前景充满恐惧。
对我来说,大学四年,好似生活在奥威尔所说的“巨鲸的肚子里”。我只感到黏糊糊的窒息,但绝没有勇气逃离,弱小到甚至都没有能力摆出个桀骜不驯的样子。如今,我可以超然地再看那段经历,才发现那是我习惯性忘恩负义的开始。
3
幸运的是,快毕业的时候,我如愿考上了一个文科大学的研究生。尽管新的环境也很正统,但毕竟是文科学校,课程有趣得多,和同学也能有更多的交流。更关键的是,再不需要为毕业分配的事情发愁。我长高了一些,开始和女生交往,但我喜欢的人,都觉得我不够实实在在。
八十年代,被很多亲历者浪漫化了。这也难怪,那是很多人的青春,那个年代记载着精英们的憧憬和辉煌。对我来说,它只意味着有出走的可能。这次,我知道自已要离开什么,正如崔健所唱:
望着那野菊花,我想起了我的家,那老头子,那老太太,咿呀。。。
没有花房姑娘问我要去何方,我也不知道大海的方向。当我读完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走,就是要离开,去哪里都无所谓。
很多年后,读了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和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原来,青春年少,不只是我这样的弱小者才会想到出走和离去。“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对于年轻人来说,出走,有时候只是想离开一个地方,并没有真正的什么目的,更不见得是由于什么远大的理想。我不知道我是谁,我需要用旅程来定义自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至于奔向什么,寻找到什么,一切都是未知。
所以,那时的离开,不是因为惧怕于暴力,而是由于青春不可抑制的渴望。我是那个年代的幸运儿,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我告别了北京,目的地伦敦。
4
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似乎总是有那么一条橡皮魔力带,不管你走多远,都要把你拉回来。世世代代几乎所有的出走者,都被系在了这条橡皮带的一端。
只要归来,就一定不再是少年,这不是因为赘肉已经在腰间积聚,也不是因为发际线开始后移。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农村的人来说,最初的离开,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色彩,而八年之后的回归,则是彻头彻尾功利主义的算计。
归来,意味着决计要入围,意味着要以一种所谓成熟的姿态,对这块土地上的规则给予认可。多年未见的大舅电话里问了我一句话:你小子要回国混了?一个混字,道尽了归来的主题。
此后若干年,娶妻生子,买房购车,我按部就班地完成着人生的规定动作。当下是饭局、红酒和雪茄,远方是三亚一个面海的小公寓,未来是麻将、旅游或高尔夫。
清点着善良人们的点赞,我感到空前的绝望。
那曾是一个漫长、充实、热闹的岁月,回头看,我所有的奋斗和享乐、所有的得意或焦虑,都和他人无异。在这样的岁月里,人可能会出轨,但不会脱轨,不会逃离。逃离,意味着失去积聚的认可,意味着失去存在的意义。
那些年里偶尔也会想,人活着为了什么,但随即就会用酒精和忙碌来冲掉这些不打粮食的质疑,甚至嘲笑自己少年时代的多愁善感。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你不会觉得害怕和孤单,也不会想到逃离,只会慢慢迷失自己。
霍珀作品,纽约房间
5
2009年的夏天,在北京八号公馆最大的包间里,我参加一个聚会,投行精英们左拥右抱,把酒狂欢;此后某个失眠的夜晚,坐在宋庄那个租来的农家小院里,如水的月光洒下,只有大狗白熊蜷缩在我的脚边。那是一个矛盾和犹豫的夏天,那是我再次逃离的开始。
因为胆小、没有魄力,我被追随多年的大佬Big先生冷落,必须另谋出路。
回上海面试,小学毕业的老板循循善诱地对我说:您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去大学当老师。
回老家看母亲,被拉到一个饭局,主人是当地著名企业家。他指着我说:“这位高中时和我同年级,当年是我的偶像!”他的话,让在座所有人都对我报以同情的尬笑,每个人端着酒杯过来,都说要敬“偶像”一杯。
这些小打击不算什么,仍然有大把的机会。但在那条熟悉的道路上,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什么悬念。失意给了我逃离的借口,可是,年纪越大,越容易沉积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越容易纠结于当年某个偶然选择的成败 – 所谓的事业,所谓的关系,是一片沼泽地,也是一个舒适区,逃离谈何容易?
辗转十年,当我终于重新找到大学校园里那个迷茫、柔弱、孤寂的少年,面对他,无言以对,羞愧不已。
前些天,Big先生投资的某上市公司因为行骗被曝,和他很熟的一位金融界人士乔伊跟我谈起此事。乔伊感慨诚实的重要性,对我说,我们没挣那么多钱,但我们至少可以为自己的诚实骄傲。
乔伊的话,让我觉得惭愧,当年为Big工作时,我只有对某个人的忠诚,但没有对良心的诚实。促成我逃离的,不是有意识的诚实,而是不自觉的胆小。被冷落之后,我感到的是失落,怀疑自己的人品和能力,甚至懊悔为此失去的机会。
因为胆小和失意而逃,不值得骄傲,只是走运。
6
2020,我们终将各奔东西。这是元旦前夜,我在新公众号上发布的第一篇文章。
那天凌晨两点,打开公众号后台。突然看到,文章标题从黑色变成了暗灰。我意识到,就在这个瞬间,文章没了。我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的敏感,就这样,存活了三个多月,最终还是被灭。
这肯定不是机器干的,此刻,肯定有一个人在暗处,他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手起刀落,毫不留情地按下了删除键。
这么晚了,我没睡,他也没睡;我在明处,他在黑暗里注视着我。尽管我可以嘲笑他如电影《别人的生活》(又译《窃听风暴》)中的威斯勒,尽管我可以原谅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可否认,他和他代表的力量无比强大。他可以随意搞我,而我只能把拳头挥向空气。
那天我失眠了,愤怒、沮丧和厌恶的情绪汹涌而至。当窗帘的缝隙透进亮光的时候,我恍惚回到童年,体弱的我被人欺负;回到大学,再次遇到辅导员阴冷的目光;回到深夜伦敦的街头,被无赖追打。我拼命想跑,迈不动脚步;使劲想吼,可发不出声音。
梦醒,我似乎明白了该何去何从。
7
很多年前,曾经喜欢过一部动画片《小鸡快跑》。母鸡们每天下蛋,生活在鸡场里本来是很幸福的。后来等她们知道接下来要被宰杀做成鸡肉饼的时候,才开始恐惧。但真正能蛊惑她们决心逃离的,是一只在马戏团混过的公鸡洛基。
我想,当她们逃离后在远方的山坡上吃草捉虫的时候,她们该如何回忆当年的鸡场?她们是否会怀念那美味的鸡饲料?她们是否还会关心那些没有离开的鸡?
事实上,根据我在鸡鸭方面有限的知识,骚狂的洛基很可能早就在鸡场里被举报,第一个被绞成肉饼。因为母鸡们认为,只要她们坚持按部就班地下蛋,勤勤恳恳地孵育,主人没有理由不善待她们。洛基的出现,搅乱了她们的好梦,焉能不死?
即使洛基不被清除,他顶多也只能带着那只爱他的鸡逃走,而所有其它的鸡都会在背后恶狠狠地谩骂、诅咒他们的背叛和逃离。
更大的可能是,没有一只母鸡愿意跟他走。但对洛基来说,其实这又何妨,只要飞出去,天涯何处无野鸡?
8
上学时,学习成绩好,会受到称赞。现在回想起来,那只是会考试而已。跟考试总不及格的同学打扑克,我从来都没赢过;象棋和围棋都学过一点,但下不过锄地的大叔。我见识过乡下村干部的政治智慧,也目睹过二十来岁理工科大学生的积极向上,个中技巧之高,令我膛目结舌。
放眼望去,周围都是聪明人,吃喝笑骂,嘴巴都没闲着,每个人都快乐。
想要改变的是傻子,是情商低,聪明人满腹经纶、学贯中西,他们在糊涂与清醒之间,在理性与热情之间,切换自如,随机应变,永远都能自圆其说;不如意的是坏人,聪明人也会义愤填庸,也会嫉恶如仇,转身割起韭菜,毫不留情;不合群的是失败者,明白人经营着圈子,抱团取暖,资源共享,流量互换。
所以,不需要说什么,没有人需要唤醒,没有人需要拯救,世界充满快乐,痛苦是一种罪孽。
鲁迅曾经写道: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他不是蒙昧的非洲土人背着雪亮的毛瑟枪,也不是疲惫如中国绿营兵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这个时代,再不需要投枪,四周都是亢奋的人群,你不知道该掷向哪里。转瞬之间,你会被包围、被缴械、被踩踏,毫无生还的希望。我所需要的,可能只是一颗火柴,点亮内心的一盏小灯,当于夜路狂逃之际,还能有那么些许的光亮。
霍珀作品,夜行者
9
写到这里的时候,又是深夜。一个未见面的朋友向我要“各奔东西“的原文,问我:我们会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吗?
我回复:试着忘记我们。他说:多谢提醒。
有一种逃离,是灵魂出壳,是心理出局,是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不需要远走高飞,不需要归隐田园,不需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只想住在旧城的闹市一隅,因为我热爱这人间的烟火气。街角的便利店,门口的水果摊,小巷尽头的菜市场,阳光下的咖啡馆,都让我感到寻常而蓬勃的生生不息。
这些不都是似曾相识、随处可见吗?在伊斯坦布尔,在巴黎,在纽约,在那不勒斯,在孟买,在清迈,在里斯本,在上海。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
年轻的时候,一心要背起行囊,走上大路;而终于有一天,你会认识到,你站立的任何地方,都是你自己的船,都能把你带向彼岸。那里,可能有你最需要的珍宝:谦卑和孤独。
人们总是膜拜那些顶天立地的斗士,嘲笑逃兵和那些无根的游士。对此,我已坦然。几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从非洲启程,跌跌撞撞,何曾停下脚步?逃离是人类的宿命,流浪是宇宙的真相。我逃,故我在。
2020.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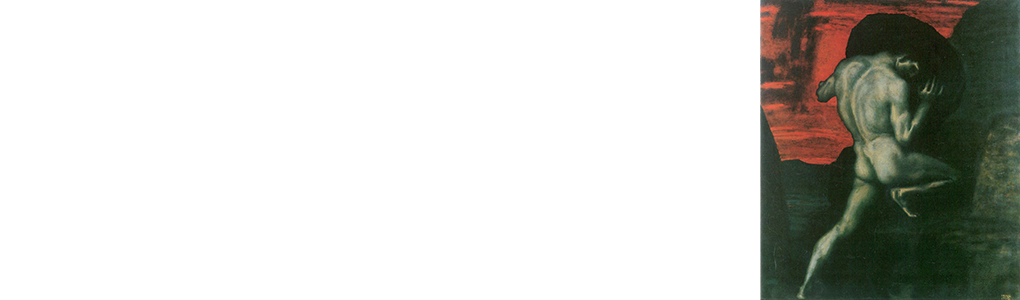
《我逃,故我在》有1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