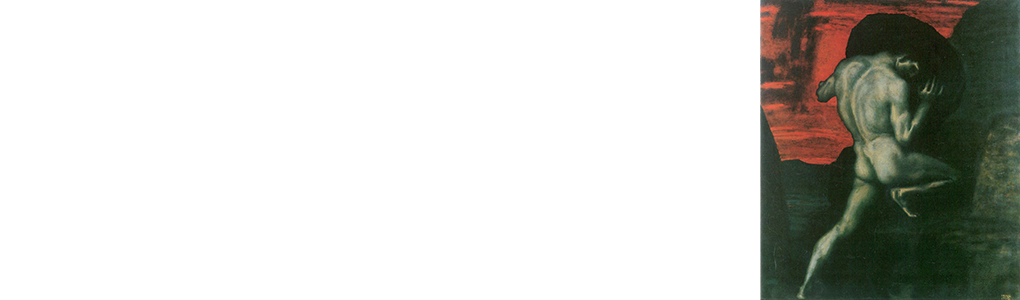复活节假期,女儿跑去伦敦的海伍德美术馆看展览。她发来图片说,达米安-赫斯特的展厅里,挤满东方面孔的年轻人;而露易丝-布尔乔亚的展厅,更多是西方面孔的老年人。我把图片转发给跟我学过英语的小柠檬,她妈妈说,2018年,她们在上海的龙美术馆看过露易丝-布尔乔亚的展览。
上海2018,听起来恍如隔世。
达米安-赫斯特最新的展览在东京国立美术馆,此时那里正展出他疫情两年中创作的“樱花”系列,每一幅作品都至少有一层楼那么高,画面狂野饱满,生命短暂而绚烂。是啊,四月的日本,该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吧?
四月的上海,窗外春光明媚,我正在被封闭着。女儿很贴心,关切地问是不是储存了足够的食物。我说,我这里都好,第一天足不出户竟然还有些新鲜感。你给姑姑打个电话吧,她住在一个叫浦东的地方,封起来已经二十多天了。
封起来二十多天的朋友还有几个。前几天我给住在闵行的老任送菜,他从家里出来闯到大门口见我,头发老长,一脸怒气,差点和保安干起来。麻辣隔壁,关了二十多天,也不给个说法!老任的状态,和开始被封的那几天已经大不一样。兄弟啊,你好天真,行动主义时代,没想法,没说法,没办法,只有让你欲哭无泪的做法。
浦西封闭之前的十来天里,我开车帮三金的餐厅送外卖,曾几次到过闵行和浦东。几乎所有的店都关着,路上没有车,昔日热闹的街道一片死寂,感觉很是魔幻。沪光路上,有个小区门口停着救护车,对面小区门口的保安说,这里已经封了一个多月。至于什么时候才能解封,没人知道。
傍晚,我们送饭到江桥一个被关二十多天的社区门口。走近突然发现,黑乎乎铁栅栏的背后,黑压压有很多个戴着白口罩的头,沉默中注视着我们,同一样的漠然的眼神,如同旧照片中的饥民。保安说,他们在等送菜过来。起风了,天要下雨,路上的购物袋被吹起,大门口红色的横幅刮落到地上,末日的气氛令人心悸,我和三金匆匆离去。
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体验被封这么多天的感觉。但接下来我们自己最终会被封多久呢?我不知道。从被关的那天起,我开始不刮胡子。倒要看看,解封的时候能留多长。
实际上,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太多了。
2004年来上海后,我常去老任开在复兴西路46号的爵士俱乐部,此后又多次去过他的爵士音乐节。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是2016年复兴西路店关门的那一天。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他在上海的爵士事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开在红坊的On Stage关了,然后豫园万丽酒店楼顶的JZ Latino关了;去年,青海路的Wooden Box也关了。这几年爵士音乐节的规模越来越小,此次疫情之后,巨鹿路的JZ Club还能撑下去吗?
还有那无数的已经被关了将近一个来月的餐厅,有多少能熬过这次疫情结束?
据说外地的人们都在观望上海,可新冠病毒不听指挥,无组织无纪律,专治各种小人得志和幸灾乐祸。看当前天女散花似的传播,下面会飘去哪里呢?没人知道。
更何况,嗨,上海人民开心的事情可多了!别的小区先封了,我们这些当时还没封的就很开心,抢到很多蔬菜装满冰箱也很开心,社区发的东西比别人的好就更开心。浦西封之前的那个傍晚,所有的店提前关门,货架空空如也,街上行人寥寥,人们都说找到了久违的过大年的感觉,纷纷亮出年夜饭。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比我们更会寻找幸福呢?
我认识一位女士,家里狗狗平素只在楼下的草地上拉臭臭。这次被封不能出门遛狗,据说她专门买了一片真实的草坪铺在自家的客厅里,给狗狗做临时厕所。这样的精致,这样的爱心,是不是只有在我们上海才能找到?
那几天送外卖,途经的地方,既有郁郁葱葱中寂静的高档住宅,也有密密麻麻杂乱的普通居民小区。路上,三金说她心里很不踏实:餐厅几个男员工将要住在集体宿舍里,每天这样熬着,多无聊。的确,如果这样一直关下去,住大房子的人还好忍受,而那些在狭小的空间里寄栖的打工者们,没有收入,不知下一步落在哪里,他们会怎么度过呢?没法想象。
今天,上海检测出阳性的数字超过八千。浦东和闵行封闭近一个月之后,数字仍然居高不下。从这样的状态到清零,还会有多久?恐怕没人知道。
还有,即使上海不惜一切代价,最终清零,但病毒并不会走,不知哪会儿又从哪里冒出来。到那时该怎么办?再一次封城?这样反反复复,什么时候才能回归正常?
被封前一天,为了分享一些封闭期间的资讯,我拉了一个上海亲友群。之所以起名叫欢乐群,是因为我的确生怕封太久会抑郁。有位朋友说,写点幽默的东西吧!可怎样才能幽默呢?我不知道。
我真的笑不出来。当看到那些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夺走送去隔离,愤怒无以言表,扎心一般地痛。在这件事上,所有的、所有的参与者,都与畜生无异。加缪在《鼠疫》中说,我到死都不会爱上这个让孩子们遭罪的世界。今生我还有可能再说自己爱上海吗?我不知道。
但我也无法悲愤,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读到的信息,只能用“荒唐”来形容,你无法相信这些会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国际一流的上海。面对荒唐,又该有什么样的表情呢?
不,绝不应该再是悲愤。这个民族的情绪,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悲愤,然后是一次又一次匆忙的忘记。从悲愤中获取自己内心的和解与安宁,难道不是智力上的懒惰,难道不是面对良心的怯懦?
或许,我们真的需要幽默,让幽默击穿荒谬。来点冷冷的、黑色的幽默,让我们从摇头苦笑,到微微冷笑,也许可以未来会心一笑,那是否有一天也能哈哈大笑?我不知道。
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知道。刚看到聂鲁达的话:假如我们不是一根筋似地让生活前行,而是哪怕只有一次,停下来啥也不做,也许巨大的沉默可以中断我们从来都没有自知之明的悲哀。
封闭中,我们还在尽量地去找事做,去忙碌;街上没有汽车的声音,但我们也并没有沉默。叽叽喳喳,我们急切地彼此打听着,翻来覆去地猜测着,但我们是否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去追问为什么?
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接下来会怎么样,而是为什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能找到答案吗?我猛然想起了鲍勃迪伦的歌: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2022.4.3
鲍勃迪伦的《在风中飘荡》,只需要改几句歌词,就成了这个样子:
一个男人要经历多少检测,
才能被称为阳性?
对面的学校还要关多久,
我们能再次听到孩子们的歌声?
这个城市要封多少次,
沉默就会腐蚀她的心灵?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我们还要等多少天,
才能再见到亲人?
我们口袋里还剩多少钱,
直到有一天交不起租金?
我的乡亲们还要流多少泪,
才会想去发现原因?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
才能看得到天?
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
才能听到人们的哭喊?
一个人要扭头多少次,
来假装他看不见?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How many tests must a man experience,
Before you can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days must schools be shut,
Before we hear the children sing?
How many lockdowns must our city have,
Before silence corrupts its soul?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how many days do I have to wait
Before I can see my mum again?
How much money do I still have,
After paying next month’s rent?
How much tears must our people shed,
Before they want to know the reason?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And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