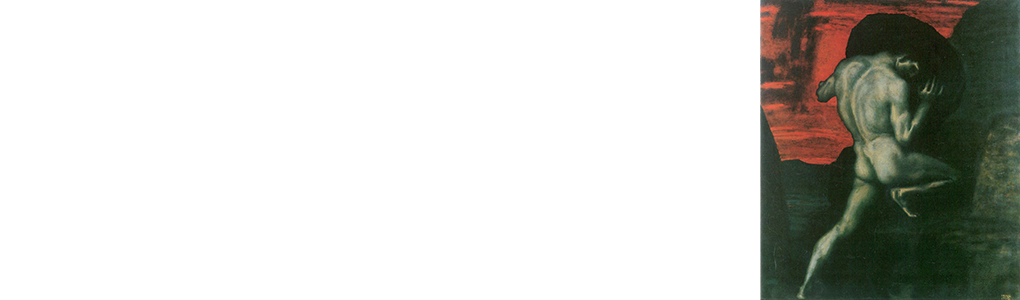琼对我说,她八十多岁的母亲在加州住了两年,想回成都,按规定要在上海隔离两个星期。隔离结束后,表妹会从成都飞过来接老人,中间住酒店接送之类可能需要我帮忙安排。为了方便联系,琼把我和她表妹拉到一个群,对她说:劳伦斯是我认识三十多年的朋友。
我说:“是的,小时候我追过你姐。”
我是在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晚上认识琼的,当时我在人大读研究生。琼只有十七岁,在北大读二年级,住在三十一号楼四层楼梯拐角处的女生宿舍。那天是个周六,清华的爱德华先来人大找我,我们没在食堂吃饭,而是出人大校门,沿中关村大街一路向北。深秋时分,这里原本四排高大密集到可以遮天蔽日的白杨树开始稀稀拉拉地落叶,公交车上挤满在香山看完红叶后回城的人们。在中关村那家简陋的延边朝鲜冷面馆,就着狗肉和花生米,我们喝了些啤酒,然后去北大食堂跳舞。在糊着彩纸的日光灯管照耀下,我发现了人群中小巧且一脸稚气的琼,抢着和她跳过一曲,打听到她的班级号,第二天就开始写信。
爱德华原名刘爱国,现在上海做投资,他那时也是十七岁。刘爱国十三岁考进清华,我去他们那个臭烘烘的宿舍找老乡时,他正坐在下铺试图解开秋裤的松紧带,嘴里嘟嘟囔囔:“按照模糊数学原理,这个扣子是应该可以解开的。”
作为文科生,我向来对数学好的人心怀崇敬,很快便和刘爱国成为朋友。因为看过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爱德华医生》,于是给他起个外号叫爱德华。刘爱国白白胖胖,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无论如何都难以和高大冷峻的派克联系起来。他很喜欢这个新名字,几十年过去了,他名片上英文那面,一直印的都是Edward Liu。
爱德华天赋异禀,他的记忆力和文学方面的功底同样令我叹服。在圆明园的长凳上,我曾听他一首接一首地背诵《红楼梦》里面的诗,直到夜里闭园被保安人员赶出。他比我小四岁,对男女之情的看法却极其成熟。毕业的时候,班级做了纪念册,每人都要回答若干问题,其中有一题:爱情意味着什么。十八岁的爱德华回答:力比多的狂欢。那次北大舞会后不久,爱德华听说我喜欢琼,摇摇头,诡异地笑着说:“你没戏,完全没戏。”
对此,当时我不以为然,如今才明白爱德华何其旁观者清。前不久,琼的年级制作三十年毕业纪念册,征集选用了很多当年的老照片,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琼。阳光下,她站在自行车棚前面,恬静靓丽,青春无敌。
从人大到北大南门,坐公交中间只有黄庄和中关村两站地,骑自行车也只要十几分钟,我并不好意思经常去找琼,而是没完没了地给她写信。不久之后,她给我回信告诉我她喜欢上同校男生,今后和我只能做朋友。那个打击巨大,我躺在宿舍床上,好多天都不想吃饭说话。
夜里我挣扎着爬起来,到中科院家属院去找小宜。小宜早已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在文学杂志社做小说编辑。我经常去他那个面南的小房间,书柜上有他和女朋友在未名湖滑冰的照片,也有汤姆-克鲁斯《壮志凌云》里和女友的戎装剧照,同样的年轻,同样的英气逼人,同样的充满希望。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小宜嘻嘻笑着说:“你肯定不是来找我要烟抽,是不是失恋了?”我们散步到计算所的操场,小宜以优美的姿势飘起,长腿跨到双杠上,背后清冷深邃的天空布满星辰。我抬头看着他,试图详细述说我没开始便已终结的爱情,他几乎马上将我打断:“这世界上有六十亿人,一半是女的,你还愁找不到老婆。”当时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信心百倍,返途刚骑到中关村320路车站,悲伤就排山倒海般地再次涌来。
那是一个令很多同龄人怀念的时代,校园内外洋溢着冲动和新鲜。除了如饥似渴地读《走向未来》那些黑字白底封面的小册子,我参加了很多校外活动,到处听讲座、论坛,参与年轻的智囊机构组织的社会调查,在杂志社做特约记者,发表幼稚粗糙的学术文章赚稿费。尽管忙碌着,每天心头挂念最多的还是琼,仍然给她写信。我经常找理由去北大,有时是和小宜等人去北大见朋友、看电影或跳舞,更多时候是在冬天的早晨,背上我的冰鞋去未名湖滑冰。不管因什么理由而去,不管和谁一起去,我都想着能和琼不期而遇。
事实上,我并没有放弃,仍然以各种理由去找她。我们曾和爱德华一起,坐绿皮火车到怀柔去爬残破的野长城;我们曾在冬夜里跑过未名湖寂静的冰面,摔倒再爬起来;下雪的日子,我们在校园里堆起令路人驻足惊叹的雪人,我为红衣的她拍下雪中留影。此前的那个夏天,小宜的同班好友老赵,那个心怀报国大志的年轻人,已经在怀柔水库游泳时溺亡。许多年后,读纪念诗人一禾的文章,才知道老赵的骨灰,被朋友们悄悄埋在了未名湖向阳的堤坡上。就是坐在这个堤坡的枯草上,在一个暖融融冬日的下午,我不无炫耀地滔滔不绝,讲我在参与的那些貌似宏大的事情,讲振奋人心的未来。琼恍惚地听,既不赞许,也不反驳,太阳在冰面上洒下一片银白色的反光。琼的沉默让我不安,似乎能自觉某种风暴欲来的浮躁。我隐隐地绝望着:这个如梦一般朦胧的女孩远远比我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里,好像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考托福出国。那时托福的满分是六百四,爱德华考了六百二。我跑去把这事告诉了也在准备考托福的小宜,他说:“托福考六百二的人脑袋一定有毛病。”2007前,去北京参加小宜的遗体告别仪式,望着他那被化妆师修正过的已经与他本人完全没关系的脸,我强忍泪水,心里愤愤地骂:“操你大爷,你脑袋才有毛病。”
北京多风多沙的春天总是很短,柳絮飞扬的日子结束,夏天就到了。爱德华收到几乎他想报考的所有顶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后选定哈佛去了美国。琼本科毕业继续留在北大读硕士,我研究生毕业后加入了向往的研究所。琼有了新的男友,我也在和音乐学院弹钢琴的女生交往。一个傍晚,我收到琼的电话,她放假回成都,买不上火车票,问能否用我的记者证帮她买张票。我回复她说,火车票太紧张,我那特约记者证不管用。听她悠悠一声叹息,无可奈何地挂上电话,我越想越觉烦躁,赶紧骑自行车从苇子坑到人大东门右侧的火车票售票点。站在那里排队到凌晨六点,取得发号后,又骑车到北大找琼拿着学生证来买票。东方即白,夏蝉鼓噪,当我在宿舍楼下喊她名字的时候,琼一定是以为我犯了某种病,从窗子里探出头,颤微微地问我什么事。我告诉她已经排队拿到了号,需要她带着学生证去购票。骑车去售票点的路上,琼一路无言,我回宿舍倒头而睡。后来每次谈恋爱,我都会在适当时候漫不经心地跟女生提起这事,但我发誓这绝不是那天晚上整夜排队的初衷。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出走的年代。爱德华拿到哈佛录取通知书后,跟我建议办个收费的出国培训机构,肯定可以赚钱。他这个设想,比新东方的成立早了很多年。我把这个建议告诉小宜,他说他自己也在复习考托福。这时候,研究所给了我一个去伦敦做访问学者的名额,考虑到出去一年半载可以省下不少钱,我立即放弃了所有创业的打算。临行之前,我去琼那里告别,她悄悄跟我说,她也在准备考托福和GRE申请出国,我们约定,互相写信。
再一次见到琼,是十年之后。她从加州大学毕业后在硅谷找到工作。那些年里,虽然已经有了Email,我们仍然主要靠写信保持联系,每封信都写很长,谈彼此职业发展很少,谈各自感情波折甚多。1998年春天,我已回国工作,琼专程回北京参加北大建校一百周年校庆,我穿上小宜送的印着“北京大学”几个字的套头衫去机场接她。当我们张开双臂,扑向对方的时候,北大校方的摄影师举起了相机,没考上北大也没追到北大女生的创痛,在那一刻多少获得些慰籍。此后我去美国开会,琼专门请假一周,开车带我沿着一号公路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那是一次轻松的旅程,我从纳帕山谷小杯的红葡萄喝起,直到几天后在拉荷亚大碗的玛格丽塔中沉沉醉去。依稀记得在桑塔莫尼卡的沙滩上,我们赤脚临海而坐,对面是看不到的祖国。我转头望着琼,她正眯眼注视着前方,太平洋金黄色的落日映照着她坚毅柔和的美丽面庞。此生和这个女孩走近些,也许不至于犯太大的错误。我当时想。
事实上,那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大错,甚至从不去想何为对错。现在回看,同时代不少人已功成名就;也有不少曾经风光的校友、同学进去了,这辈子都放不出来。为此,爱德华和我经常唏嘘。几十年来,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们一起聊赚钱,一起愤世,一起变胖,两家年年相聚,孩子们一起长大。他太太琳达心里很清楚我是爱德华最好的同谋和掩护,我知道他所有的浪漫故事以及他们夫妻之间的长期战争,但信佛的人的确不同寻常,每次见到我,琳达仍然是温文尔雅、热情有加。爱德华二十六岁那年,从哈佛同时获得经济学和法律两个博士。他先应聘回国在北大当了一年学者,娶到系花级女硕士琳达后,转头又回美国到华尔街做投资。我问他为啥不像他得过诺贝尔奖的导师那样坚持做学问,他很坦白,回北大做学问只是因为性饥渴和寻偶冲动,而“弄个诺贝尔奖也就是那么回事。”这可能有些道理,爱德华赚的钱早已远远超过诺贝尔的奖金。只是最近几年,每次约他吃饭,我都希望和我见面的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不是一个已经秃了头的投资人。
近来爱德华很抑郁,这并不是因为头发的稀少,而是暗中相交多年的“真爱”绝然离开。我见过一次这位做理财顾问的明显整过的真爱,比爱德华小二十多岁,身材高挑,凸凹有致,的确好看。据说最终分手场面很难堪,真爱鄙夷地宣布他们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爱,爱德华于是感觉上当受骗,而真爱同样痛悔和爱德华一起蹉跎了青春岁月。还好,爱德华和已经皈依的琳达并没离婚,他们的孩子都已去国外读大学。那天酒后爱德华对我说,每次驱车要回到他郊外那有内部电梯和豪华佛堂的别墅,内心都会无比沉重,无尽迷茫。“你看,我养了这么多人,最后所有人都恨我。什么都不缺,可心里总觉得空空的。有时真想,还是小宜明白啊!”他酒后这些车轱辘话,我似懂非懂,也并不太当真。我对他说,至少我永远都不会恨他。的确,我们就像连体兄弟,被下了同样的咒语,中了同样的毒,酒色和哥们儿救不了我们,没有任何别人能救我们。
可小宜又明白了什么呢?他有数不尽的朋友,喝不完的大酒,我对他素来仰视,无法真正亲近。年轻时我觉得,做文学编辑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职业,能有小宜那样的天资是上天最大的眷顾。他曾经带我去过王朔在军队大院的家,我曾经在他家那个小房间里读过后来几部出名小说的手稿。他和发小们踢球回来,我愿一边给他按摩大腿,一边似懂非懂地听他谈东论西。有次说到古龙,他问我最喜欢哪个人物,我说当然是陆小凤,他拍着我的肩膀:“嗯,他跟我一样,从不放过任何中美人计的机会”。小宜后来没有出国,而是选择去下海经商。我很怀疑这是不是他应该进入的世界,但他会做别的选择吗?在商业世界里,他总是显得风光无限,志得意满,他的好人缘和机智幽默更令人艳羡。不过我总隐约觉得,他身上永不消失的酒气,也许诉说的正是他的孤寂。克鲁亚克说:“我只对那些疯狂的人感兴趣,他们疯狂地活,疯狂地说,疯狂地得救,他们同时渴望一切,从不打哈欠,从不絮叨家长里短,他们只是燃烧、燃烧、燃烧,如绚烂的黄色罗马蜡烛爆炸,炸出无数的蜘蛛洒落星空。”不管怎么说,对我来说,小宜就是那个疯狂的人,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真正地燃烧过的人。只是,他燃烧的地方过于阴冷黑暗。他是个厚道人,他让所有的人开心,Everyone took a little piece of him,最终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在一个柳絮飞扬的春天,小宜迎着朝阳,挥手离开,他和克鲁亚克共享的,是同样的终年。
冬天到了。冷不丁看下日历,突然意识到这天是小宜的生日。此时未名湖应该又一次结冰,我想起了曾看着我摇晃着滑过冰面的琼。她一直留在硅谷,和同班同学相爱结婚生下一女一儿,正好和我两个孩子同龄。前些年他们回国,我们两家几乎每次都要相聚。孩子们现在都已上大学,琼也拿起了相机。同龄人玩摄影的越来越多,但只有琼的作品最清澈真诚,我能感受到她婉约含蓄的灵气和从不动摇的认真。她跋涉到北美很多地方,照片里都是我不曾见过的风景,不,即使见过,我也不会有琼那样的眼睛。写到这里,我发消息问她是否拍过北大校园的照片。“以前的还是现在的?18年回去参加校庆拍过一些,不过都有人。”她很快回消息,发过来两张照片,一张是中年的她坐在湖边的长椅上,一张是她十四岁的儿子坐在同样的地方,瘦高的少年憨笑着,满脸诧异。“当年有次下大雪,你曾经给我在这里拍过,这还是那条长椅。”
已经很多年没去过北大了,我打量起手机屏幕上她发来的这两张近照。未名湖已不完全是记忆中的样子,湖面似乎大了很多,新注的水已经淹没了三十多年前我们曾经坐过的斜坡。远处角落的博雅塔笼罩在薄雾之中,背后是阴沉沉的五月天,湖水的中间映照着天空的灰白,与垂柳深绿色浓密的倒影相连。岸边,青草萋萋,野花怒放,生命美丽而坚强。
2021.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