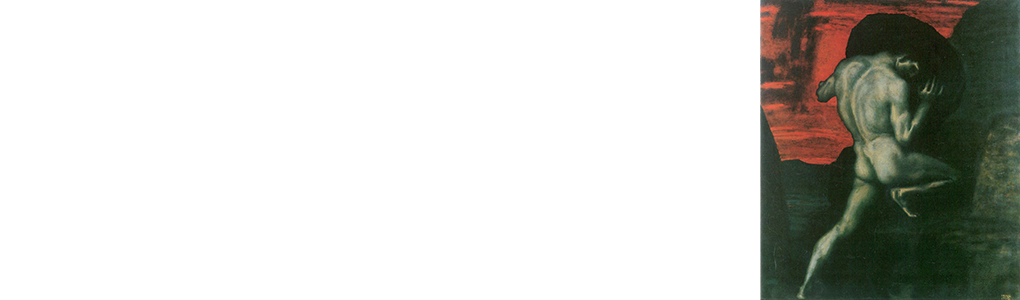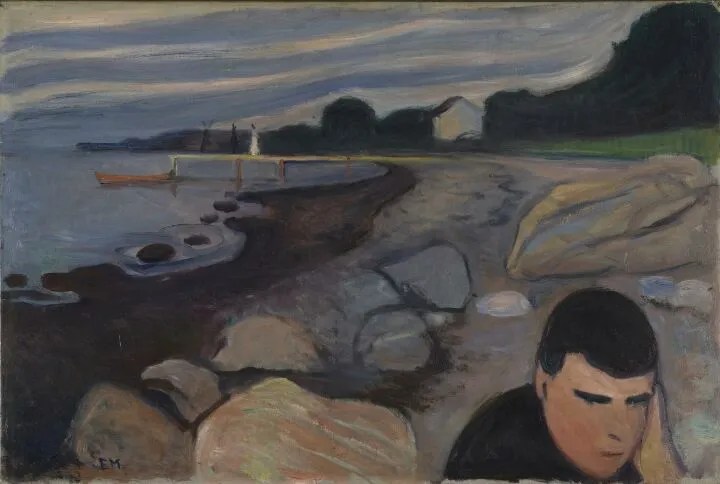
1
母亲膝盖动手术的事一拖再拖,直到那天腿疼得不能走路,她才答应住院去除掉骨刺。在老家市里的弟弟妹妹都有公职,请假不容易,于是不用坐班的我特意从上海赶回来,作为家属陪护。
名义上我是陪护,但二十四小时陪在母亲身边的,是刚来一个多月的保姆霞姐。之前几年里,母亲换过好几个保姆,为此让我小妹操透了心。其实母亲绝不是那种难伺候的老人,她对卫生情况并不介意,和前面几位保姆的冲突都是由于她太节省。有时她会责怪保姆太浪费,比如洗澡时间太长,出门买回来的菜太贵;有时保姆则会对小妹抱怨总被母亲盯着,伙食还不如在自己乡下的家里。
我对母亲的节省无可奈何,其中最烦她从来不把吃不完的饭菜倒掉。她会一顿接一顿地热,直到吃完。每次跟她说剩饭菜对身体不好,她就在那里喊:“俺都八十好几了,俺才不怕死!”上次回家花十八元买了三个素馅煎饼,我要把最后剩的半个扔掉,她死活不肯。我说带走到火车上吃,她真的就急了:“你到火车上也不会吃,肯定是出门就扔!”没办法,我只好留给她。我问她:“您知道我每次坐高铁回来看您,要花多少钱吗?”母亲说:“你愿花钱是你自己的事,跟俺没关系。”
这次住院,我对母亲的英雄主义却有了新的认识。第一个晚上,主刀的张大夫反复安慰,这是个微创小手术,打麻药后不会疼,但母亲仍然被吓得一夜没睡着,导致第二天血压升到高压200。为确保手术安全,头天晚上给她在点滴里配上了安眠药。
母亲很满意自己的退休工资,她不缺钱。我能理解她们这代人,抠门的习惯已铸进了骨髓。她们经历过长期的贫穷和饥饿,而饥饿的折磨最痛苦,记忆也会格外深刻。更何况,节省意味着热爱生命,向往未来;节省的习惯让她依然还保留着我们儿时的碗盘和调羹,让每次回家感觉都好亲切。
2
霞姐能和母亲相处融洽,主要是因为她不识字,不会像前一个保姆那样,整天抱着手机玩。她很愿意陪母亲聊天、玩牌,同时吃饭也是越省事越好。谁能想到,母亲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年纪大了,身边陪她的却是个文盲。不过,前几天母亲说,她已开始教霞姐认字。
霞姐又矮又瘦,满脸皱纹。她其实比我还小,霞姐是我小妹对她的称呼。由她照顾母亲我是放心的,但又觉得她有些太懒。住院那几天,我从医院食堂给她们带饭回病房,食堂用来装粥菜的都是那种很薄的塑料袋。霞姐没有准备碗,她只是将塑料袋直接套在一个外卖的塑料餐盒上,吃完后把塑料袋扔掉,餐盒也不洗,留着下次用。我看着心里不舒服,从超市买回几个瓷碗给她们用,但霞姐仍然只是把塑料袋套在瓷碗上,这样就可以不用洗。看她这么能凑合,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有一天霞姐不在身边,我问母亲:“她怎么会不识字?”母亲悄声说,穷呗!霞姐不仅没上过学,而且和她男人是“换亲”。也就是说,霞姐自己的哥哥们找不到媳妇,当年要用不到二十岁的她去和别人家交换。这种情况我并不陌生,在老家农村读小学,听说过很多类似的安排,比较高级的是三五家“串”起来换。
我想起上学前有个伙伴叫爱军儿,兄弟四人,中间有个妹妹。有一天和他一起玩,我在废弃猪圈的草丛里发现一只鸡蛋,兴奋地跑回家,看家里没人,就把鸡蛋埋在门口的沙土堆里,转身去学校找我妈。等和妈妈回到家,鸡蛋已经不见了,偷鸡蛋的只能是爱军儿。后来我找到他,学大人的口气大骂:“操你祖宗八辈儿,你们家断子绝孙儿!”
爱军儿长大后没找到媳妇,用妹妹换回的姑娘给了他们兄弟四人中被公认最“精”的老二,这样更有利于传宗接代,将来给几个兄弟送终。我的小伙伴当中,这并非个例。前些年我开车带老婆孩子春节回老家上坟,每年都能在村头看到爱军儿和别的男人一起抽烟晒太阳,身上总是穿着同样皱巴巴的迷彩外套,打招呼也总是同样一句:“回来啦?”
住院几天,我和霞姐没说过几句话,每次进病房,她都在和我妈或临床的大嫂叽叽喳喳聊天,看上去欢天喜地的。我从妹妹那里得知:霞姐的老公有些痴呆,两个儿子中,大儿子快三十了,身体不好,脑子也不好,这辈子估计要打光棍。现在乡下男多女少,如果在县城买不起楼房,这辈子几乎注定娶不到媳妇。
3
病房里有三个病人,母亲的53号病床是进门第一张。靠墙的地方,有张窄小的简易铁床,霞姐可以睡在上面,这可能是托人打过招呼的缘故。另外两张病床的陪护人员只能通宵睡在床头的金属椅上,根本无法躺平。
临床54号的大嫂也是五十多岁,因为是大手术,已经住院十几天,平常照顾她的是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儿。母亲手术结束后,需要将她从手术床平移抬到病床上,我自己根本做不到。小伙子很热心地过来帮忙,他负责上半身,整个过程几乎完全要靠他。后来我注意到,每天有病人完成手术后回到病房,护士就在走廊里喊:“54号的,过来帮个忙。”这时,小伙子哪怕在躺椅上打着瞌睡,也会立即站起来。
我对大嫂说:“你儿子真好,多大了?”大嫂回答,虚岁二十八了。我冒失地问了一句,结婚没有?这时大嫂开始叹气。简易床上的霞姐乐呵呵地说:“这么俊的小伙子,不用发愁,媳妇儿好找。”大嫂扭过头去,什么都没说。
大嫂的男人有时会过来替班,让儿子去城里的亲戚家休息一下。男人说,现在条件好了,农村人也可以享受医保,能承担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住院费用。家里两个老人,小伙子下面有个妹妹在上高中,大嫂生个病,家里积蓄也就光了,闹不好还要借债。男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愁容满面:“那有嘛办法呢?咱庄稼人过日子,不就这样吗?人在就好,这要赶上老时候,还不要瘫一辈子?”
母亲出院的那天,大嫂已经可以在儿子的搀扶下,在病房里来回走。我推着轮椅出门,突然想起没跟大嫂他们告别。母亲说:“不用回去说了,反正不会再见了。“好吧,我想也是。
4
刚来那天,因为折腾核酸结果,在酒店放下行李赶到医院时,已经是晚上七点。此前母亲在弟弟安排下,完成了各种手术前检测,只等我到了为第二天的手术签字。主刀的张大夫依然在医生办公室等我,面上虽有愠色,但他还是详细地对我解释了母亲的病情以及可能的突发情况。
医院里的条件看上去都很现代,只是医生办公室的装修简陋而且拥挤,桌子上摆满了电脑,四周有些我搞不懂用途的设备。张大夫是山东胶南人,四十来岁,毕业后就在这家医院工作。刚巧我多年前的公司在胶南有工厂,于是我们聊起当地的海鲜之类。离开的时候,我再次道歉让他久等,张大夫说:“没事儿,等下我们党员还要政治学习。”我和张大夫互加了微信,他的头像下角有面小国旗。
接下来几天,只是傍晚张大夫带着护士们查床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他。其实每天早上不到七点张大夫就要上班,例行查床之后,八点钟上手术台,下午三四点结束一天的手术后,再回到办公室写报告,签发出院文件,下班之前还要再次把所有病人检查一遍。家属们都过于焦虑,会问很多问题,张大夫不紧不慢的声调,很让人安心,但这也肯定耽误了他下班的时间。
当医生,真的很辛苦,我肯定做不来。
母亲出院的那个上午,我给张大夫发微信:“非常感谢!我母亲手术后感觉良好,恢复很快。去您办公室几次,想当面致谢,您都没在。”
晚上八点,才收到张大夫回信:“不用客气哈,我们职责所在,应该的。”
5
这次回家,住在了我们当地最好的酒店里。多年前,我的发小儿晓武在市里当人大主任,曾经好几次在这里请我吃饭。他现在已经被关了好几年,没有任何音信。
这次入住,发现酒店变化真大。过去房间内那些宽大的皮沙发、吧台上的安全套、深褐色的大班桌都不见了,卫生间、卧室的装修几乎都和万豪无异,茶几上有一大盘各式新鲜水果。而更让我惊喜的是,第二天从医院回来,桌上有张手写的卡片:“先生,欢迎您入住我们酒店,希望您能入住愉快。看您桌上有书,我们在此送上酒店特制的书签;您床头柜上有药,我们为您多准备了矿泉水。天气凉了,您要注意保暖。”
写下卡片的肯定是早上在楼道遇到的那位满面笑容的保洁员。其实,此行在酒店遇到的每一名员工,态度都格外和善。早餐厅里除了高档酒店都会提供的中西餐点,还有我们家乡特色的驴肉火烧、煎饼和羊杂汤,每个制作区的厨师都会站在那里主动问候。可以说,相对每晚350元的房价,这次的入住体验绝对超值。
次日再遇到保洁员,她热情地问我有啥需要。“先生,如果您对我们酒店还满意的话,麻烦您在携程上给写个点评吧。”对此,我满口答应。保洁员特意提醒我,写点评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附上照片。
临行那个上午,我正在房间收拾行李,保洁员敲门,满脸歉意地说:“先生,我看了您昨晚发的点评,您忘了附照片,能麻烦您再发一次吗?”当然当然,一定重发。我允诺她。
6
那几天和我交流最多的,是开滴滴车的司机小徐。下高铁后呼叫网约车,他来接我,听说我在这里每天都要来往于医院和酒店,他建议我随时给他打电话。我们这是小地方,我不需要赶时间,况且他的车内又非常干净,我立刻答应了下来。
小徐是位九零后,以前在当地一个中外合资汽车工厂上班。疫情以来,轿车产量下降,每天原来两个十二小时班,现在改成每天一个八小时班。实际上,因为没有芯片,出厂的车也没法入库。
小徐和媳妇一样,都是独生子女,现在有个儿子,不过他们不准备再生。疫情之前他每天跑滴滴能挣300元,现在不超过150元,再加上汽油涨价,根本挣不到钱。不过小徐勤快聪明,他经常被地产公司招呼到日渐冷清的售楼中心假扮看楼客,每次也能挣到30元。
母亲出院前一晚,我从医院回酒店,小徐叹着气说:“大哥您看这路边,过去都是店面,晚上到这个时候最热闹,现在全关了,这黑咕隆咚的,都有些瘆人。这整个市里,现在也就您住这酒店客人多,别家都没啥生意了。”
小徐说的状况,我已有所耳闻。但此刻考虑最多的,却是今夜如何能睡个好觉。失眠是我多年的毛病,酒店虽然舒服,但这几天还是没睡好。
7
回到房间刚坐下,就收到老朋友爱德华的语音通话申请,我以为他又要絮叨被女朋友抛弃的事情,没想到这次谈的却是他的儿子安迪。小伙子三年前从斯坦福毕业,现在谷歌工作,年薪已经到了二十多万美元。安迪小时候跟我很熟,我有他的微信。两年前看到他在朋友圈说要去内华达州的黑石沙漠参加“火人节”,此后就再没有了消息。
“老劳啊,我现在才知道,安迪每个周末都要去看几个小时心理医生。你说我是不是有抑郁症啊?会不会我遗传给他了?你最了解我,咱俩分析一下吧!”
“哥们儿,我他妈这几天都没睡好,今晚还想找人按摩一下,明天回上海再聊,行吗?”
我能感受到他在电话那头贱笑:“哦哦哦,行!行!兄弟你悠着点哈,回头见。”
酒店康体中心的按摩技师提供客房服务。冲澡之后,我打电话过去,很快敲门进来一个胖胖的30来岁的姑娘,妆容有点浓,穿着高跟鞋。服务手册上的报价是中式按摩一个小时188,但她推荐我做服务手册上没有的推油,好像大约是388,放松效果更好。“不用了,我只是想能睡个觉,能不能这样,我预付给你两个小时中式,等你确定我睡着了,轻点把门带上离开就行了。”
她没有再坚持。收钱之后,我爬上床,技师将浴巾铺在我背上。她的手法很差,没啥力道。但我并不介意,也不想说话,脑袋里回放着这几天医院那些情景:白天乌央乌央的人流,晚上沉闷暗淡的寂静;病房里我白发稀疏的老妈、干瘪的霞姐、唉声叹气的大嫂、忙碌的张大夫;手术室里推出来挂着点滴的病人还没从麻药中苏醒,挤在走廊歪斜等候很久的家属们一拥而上……
技师停了下来,我仍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片刻后,听到她轻轻离开床边、穿鞋、拿起手包、转动门把手。关门的声音有点大,估计半个楼层都能听到。我睡不着,算了,上午把母亲送到家就回上海,火车上睡吧!想起安迪,多可爱的小家伙!夏天的傍晚,我曾陪着三四岁的他,在他们家别墅的草地上玩足球。这一眨眼二十多年,他成了硅谷精英,居然已开始把心理医生当成救星。那爱德华和我呢?多少年都混在一起找乐子,现在却整天抑郁啦,伤感啦,失眠啦,这不是病吗?我们吃斋念佛,冥想打坐,什么发心啊、行善啊、知行合一啊,都他妈Bullshit!还不就是舍不下那点屁事?我们带着谜一般的自信想当大叔,岂不知早已活成了大爷。爵士、普拉提、雪茄、单一麦芽、哈雷、半马,我们要超越,我们要放飞,哎吆吆,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我飞呀飞呀可总也飞不高!怎么可能飞高?几十年的江湖,几千年的诅咒,早就让我们断了翅膀,没有方向,没有胆量,我们只会在你吹我捧中喝高,飘呀飘,飘向那无边无际的深渊……
2021.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