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挥之不去的焦虑,那未曾活过的人生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1)
自恋、自我实现、英雄主义的哀歌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2)

死亡恐惧与现世肉体享乐主义
人生苦短,实际上是关于生命有限性和其痛苦本质的最凝练的表达。这种表达直接的结论,通常是及时行乐。既然身体总有一天要消亡,所以必须不加抑制。
诺曼-布朗(Norman Brown)认为,不受抑制的人生即是身体的享乐,是解除耻辱和罪恶感,让身体重生作为最重要的快感,人类最大的敌人是对身体的抑制。
肉体,总有一天会消失,它代表着人的动物命运,人无法避免与肉体抗争的命运。同时,肉体为人提供内在象征世界所缺乏的经验、感觉和坚实的快感。
过去三十年,谢尔登-所罗门(Sheldon Solomon)和他的同事一直致力于通过实验来验证厄内斯特-贝克尔的理论,他们的发现是:怕死,让人更加追求享乐。如果给予实验者“死亡提醒”,他们接下来的行为会更加追求物质享受、及时行乐、更多地释放自己的恶意、更强烈地寻求群体认同。
也就是说,存在焦虑、不安全感、对死亡的恐惧,会引起人们追求即时满足,追求肉体享乐,同时会让人更多地被人性中的恶所驱动,会让人失去理性。所谓智慧,实际上是一种延迟满足。
对大多数人来说,享乐主义并不是英雄主义。异教徒不明白这一点,最后败给基督教;现代人同样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把灵魂卖给消费资本主义或以持续不断的心理治疗取而代之。
肉体享乐:罪恶感与成瘾
内生自我代表着思想和想象永恒延伸的自由,而身体代表着确定性和边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难进行性行为而不带罪恶感。享乐之后所谓的空虚无聊实质上是一种罪恶感。罪恶感来自于意识到个人肉体的局限以及世界的神奇和无边无际,它不是因为幼稚的幻想,而是有自我意识的成人的现实。
身体快感解除不了罪恶感,它无法克服、而是只会加深被造物的死亡焦虑。
罪恶感的存在是因为身体向内心的自由投下一道阴影,我们真正的自我在性交行为中被强迫进入一种标准的、生物的、机械的角色,我们身体的困境和重要性被强调。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在性行为时需要得到安慰,即对方需要的不止是她的身体。她痛苦地意识到,她自己与众不同的内生人格可以在性行为中被消灭。
爱是一枚伟大的钥匙,因为它可以让个人陷入动物状态,而同时不必惧怕和带有负罪感,取而代之的是信任和保证。爱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内生自由不会因屈从于动物性而丧失。
舒适的性爱关系显然大有益处。在性爱中,假如身体和灵魂不再分离,身体就不再是我们自身的敌人。
但这里隐含着根本的矛盾:性是身体行为,而身体会死。死亡是性的孪生兄弟,能生育的动物一定会死。如果性是人类动物性的体现,那么性行为代表着有意识的动物个人化和人格的失败。从一开始,性就意味着双重否认:身体的有限性和人格的特殊性。
人人追求快乐,对快乐感觉的不懈追求使人类得以区别于其它动物。快乐的物理原理是神经系统快速释放多巴胺,成为一种心理上的奖赏,它促使人们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有一个奖赏回路系统。
随着刺激不断重复,对某种奖赏会从“喜欢”变成“依赖”,这就是上瘾,成瘾就是人们发现了某种物质或行为能带给最大快感。
成瘾者对快感反应下降,造成刺激阈值提高。得不到快乐、无法获得满足即是痛苦。对于成瘾者来说,他们需要超正常刺激才能启动其即时奖赏的快感。
西门庆的早死,来自兰陵笑笑生认识到成瘾、肉体的有限以及超正常刺激的危险,但道德学家却借此来宣传报应。更深刻的哲学探讨,应该是让西门庆进入古稀,得以颐养天年。
人生的浪漫主义方案
浪漫主义者将对宇宙英雄主义的渴望以爱的形式聚焦某一个人,爱侣成为个人实现的神圣理想,所有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都集中在某个人身上。他要生活在两个人的宇宙。
在传统的社会中,伴侣不可能是神圣的。但在现代社会,爱侣的神圣成为可能。如果爱侣具有神圣的完美,那本人也会升华。现代人在爱侣身上寻求自我实现与追求得到上帝认可并没有区别。现代人对爱侣的精神依赖,是失去精神意识形态的结果,和依赖上帝或心理医生无异。
性爱是人生问题令人失望的答案。爱侣并非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困境的完整和持久的解决方案。他一方面代表着从意识和罪恶感中的自由实现,同时又代表着对个性的否认。
个人关系带着深层的危险,即混淆身体世界的真实面目和精神境界的完美想象。浪漫之爱的二人宇宙可能是一个勇敢和创造性的尝试,但由于它依然是世上因果项目的继续,所以注定要失败。
如果你找到理想中的爱,让他成为你好坏的唯一判断,你只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映照,你的发展被对方限制,被对方吞没,你在对方那里失去自己。当你被对方的人性缺点贬低,你会感到空虚、愤怒、生命失去价值。当你混淆个人爱欲与宇宙英雄主义,你会两者俱败。
给过度投资的伴侣减值是一个创造性的行动,这有助于让我们不再生活在谎言之中,有助于重树我们的内在成长的自由,让我们不再被移情客体所捆绑。但这很不容易,因为人们更愿意为自己减值。
奥托-朗克(Otto Rank)认为:现代爱情关系的精神负担太重,人们为其赋予了太多的意义,这导致他们只能以去精神化和去个人化来应对这种关系,其解决方案是着重身体(让对方成为纯粹的快感客体)和金钱(交换)。
性的神秘性是一个浅薄的贪求,它只适用于那些已经绝望到不再追求宇宙英雄主义的人,他们把全部的意义集中于身体和现世。
从爱侣那里需要太少和需要太多一样,都会是自找失败。
浪漫者和快感者:浪漫者试图在对象的内在和神秘中寻求全部意义,视对象为智慧之源、缪斯、纯粹的动力、持续焕新力量的无底之泉。而快感追去者不在对象那里寻找绝对,她只是一个物件。他在他自己那里寻找绝对,女人只不过是用于激起活力并让其释放。
朗克对性的蔑视并非他不在意身体之爱和快感,而是他看到人无法从他自己那里得到绝对,宇宙英雄主义一定要超越人类关系。这里,重要的是人的自由、生命质量和个性。
如果将意义集中于现世,人依然会绝望,因为他们无法克服对绝对的、神秘的自我超越力量的渴望。真正的救赎只可能来自个体外部,来自上面,来自我们想象中的终极源头,来自创造的完美。
人们需要一个超我,但他们总是从近处寻找,这给他们所谓的实现,但同时会限制并奴役他们。大部分人用安全玩法,他们选择标准的移情客体,如父母、领导、爱人,他们接受文化和传统所定义的英雄主义,从而成为模范公民。
抑制与智慧
性是人类关于生命意义的迷惑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但假如人们希望通过性来回答形而上学问题,它会变成一个关于真实的谎言,成为对抗真实意识的屏障。如果成人将人生意义集中于性,他无非是重复孩子对于母亲私处的迷恋。性于是变成恐惧的镜像,变成关于人生真正问题的全部意识的虐恋。
人的身体是“命运的诅咒”,我们的文化是建立于自我抑制之上的。这并非是因为像弗洛伊德所讲,人总是要寻求性、寻求身体的快感,而是因为人首先是想通过抑制来避免死亡。死亡意识才是自我抑制的原因,而非性欲本身。抑制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才具有的。
自我代表着生命力量自身需要经验扩展和更多生命的渴望。当进化给了人类一个“自我”,一个经验的内在象征世界,这就将人割裂成二,给了他一个多余的负担。这个负担是人类获取更多生命必须承担的代价,是人类生命力量发展并到达更高体验所需付出的代价。
自我,如果需要任何成长,一定需要否认、需要与时间捆绑、需要与肉体脱离并与之对立。同样,要想真正体验身体,必须让自我隔岸观火。认为“新的人类”是灵魂和肉体能结合,其实说的不是超人而是次级人。
没有抑制,就无法生活。抑制并非世界的假象化,而是“真理”,人类唯一可以理解的真理,因为他无法体验其它。我们必须接受生命的极限和负担。
如果需要一个真实的人类体验,一定要有界限,我们所说的文化和超级自我确定了这个界限。文化是生活的妥协,它使人类生存成为可能。
马克思说,我一无所是,我什么都是。一个人可以爆发进入没有界限的宏大癫狂,超越所有界限;它也可以缩为虫蛹,成为没有任何价值的罪人。对于界定接受多少真实,或者如何设计个人能力的产出,这里没有安全的自我平衡。
成熟就是有能力看到界限和可能性之间的平衡,然后创造性地去适应。智慧就是学会延迟满足。
那些推崇无需抑制的先知们根本不懂人性,他们设想的是乌托邦。人需要移情,因为他们需要看到他们的道德观落在实处,他们需要某种支持以应对自然力量没有穷尽的轰然而入。
无数科学家如大卫-辛克莱(David Sinclair)都在试图用科学解决问题,尽量让生命延长。也许未来会有一个乌托邦,生命没有尽头,人再无生死之忧。到那时,人类可以永远活在“永恒的当下”,尽情享受快感和和平,变成真正的上帝一般的创造物。
但是,延长生命、推迟死亡并不是解决方案,因为还有会提前死去的恐惧。设想人类的寿命可以到达九百岁,如果病毒或愚蠢的事故使人的生命停留在九十而不是九百,荒诞就要增长十倍。
(以上为个人读书笔记,内容主要摘译自Ernest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本书曾获1974年普利策奖。)
2021.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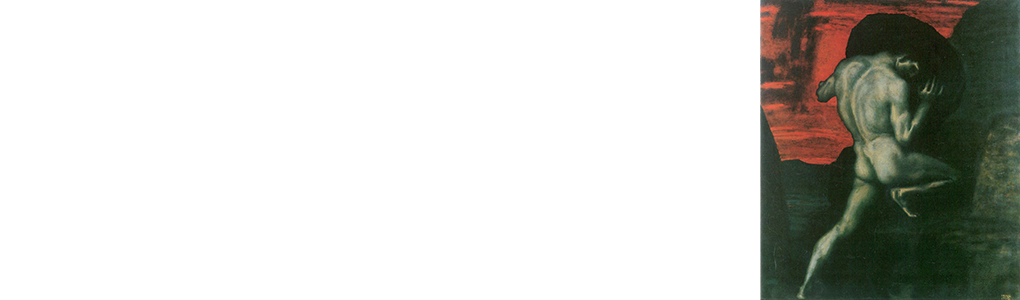
《及时行乐与浪漫至上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3)》有2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