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人皆有一死,凡人皆须侍奉。
-《权力的游戏》
大自然母亲是个残忍的荡妇,她长着猩面獠牙,毫不留情地要将她自己创造的一切摧毁。
-Sam Keen
人的死亡意识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有自我意识,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关于死亡的知觉是反应性的、概念性的、抽象性的,动物没有这种知觉。人在一生中都被这种梦魇困扰着,哪怕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十九世纪苏格兰作家亚历山大-史密斯曾经说:知道自己将会死亡,使我们成为人类(It is the knowledge that we have to die made us human)。
人是一个有象征性的自我,他是一个有名有姓有人生经历的被造之物。他的大脑可以去想象量子和永恒,可以将自已置于太虚,设想自己是自己的星球。这种无限的扩展、这种灵巧与飘逸、这种自我意识给人类本质上一个小上帝的角色。
但人是双重的,他可以触及星空,而同时又困抑于一个心跳不止、呼吸急促的身体,这个身体本来属于一条鱼,现在还带着鱼的很多特征。这个身体对他来说是一个肉体的躯壳,在很多方面与他的意志为敌 – 疼痛、流血、死亡、腐烂。
帕斯卡尔说:人类很有必要发疯,不发疯本身意味着另外一种形式的发疯。必要是因为人类存在的双重性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一个残酷的危机;发疯是因为,人类在表象世界中所作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否认和克服他悲惨丑陋的命运。他实际上将自己驱赶进一个掩耳盗铃的困境:用社会游戏、心理把戏、无休止忙碌来逃离个人状态的真实。
自然嘲笑我们,诗人活在备受折磨之中。
焦虑是人的内生设置,它来自对死亡的终极恐惧
人类焦虑是一种自然,因为我们最终将会无助地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地死去。惊慌、恐惧和焦虑是我们抵抗死亡这一基本事实的自然伴侣。
人类被授予个性化的意识,他有神性的创造、独特的自我,他同时也具有了自己将死亡并腐烂的意识,这给他以恐惧,这是动物王国最特殊、最庞大的焦虑,无边无际、如影随形。亚当和夏娃被从伊甸园驱逐,是因为他们偷吃了智慧之树上的苹果,从而具有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类的原罪,是人类受苦的根源,死亡意识是苹果核中的蠕虫。
克尔凯郭尔的折磨,来自于他看到自身作为“被造物”的真面目。一旦意识到自己是要腐烂的被造物,你就被焦虑的海洋淹没。焦虑是认识到个体状况真相的结果。人类的矛盾在于他可以意识到自己肉体的局限,意识到自己终将会成为灰烬、成为虫子的食物。这是一种自我意识带来的恐怖,来自无物和虚空。
只要人不能永生,他就永远不能摆脱焦虑。但他可以将焦虑当作泉水,来帮助他成长到思想和信仰的新天地。
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的洪水不是人的终结,而是一个学校、一种教育,它给人带来最终的成熟。被焦虑所教育意味着人要直面他的自然无能和最终死亡,意味着他要摧毁人设的谎言。
自我一定要被消除才能被发现,真正的生存一定是要感觉到自己的迷失。如果一个人不感到自己迷失,他就不会找到自己。在遗忘的边缘,他无比孤独,颤抖不已,这也是永恒的边缘。
这样就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新的真相,通过直面存在恐惧的焦虑,摧毁自我,让其成为无物,这样自我超越才能开始。
人类的失败,常因为他无法直面自己状况的真相:一个具有灵魂的自己,代表着某种自由和可能性;然而又被身体的有限性捆绑着,代表着宿命或必然性。无视上述状况的尝试,即抑制可能性或否认必然性,意味着人必将生活在谎言之中。
精神分裂来自过多的可能性,是个人过高评价自我的力量,否认身体的有限,整个人丧失平衡,从而被毁灭。身体无法容纳自我产生出来的意识自由,追逐可能性,回不到自己,造成自我和身体的分离。
精神抑郁是过多的必然性,太多的限制,内心自由不够,妥协于他人的需求,无法让自己从责任义务中脱离,虽然这些已经不给他带来自敬、价值和英雄感觉。忘记自已,不敢相信自己,等所有的事情同时变成必要而且琐碎,人便会完全绝望。带有意义幻觉的必要性是人类行为的动力,当这些变成琐碎,生命便失去感觉。
绝大部分人属于平庸主义者,介于抑郁和精神分裂之间,总是避免失去平衡,追求社会规范,让自己的人生填满忙碌与琐碎。
存在焦虑与人类行为的动机
在所有驱动人的因素中,最根本的就是他对死亡的恐惧。寻找生命的意义、追求英雄主义是这种恐惧的自然反应。
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我们要控制自身焦虑的生物性需要,是要否认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恐惧。正是因为认识到身体在时间上的有限性,人才不遗余力地要给自己的生命找到某种意义。
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如此庞大无边、如此不可忍受,我们努力将其忘记,视而不见。我们将自己困据于人设防御体系之中,冀望抑制身体来换取永恒的灵魂,牺牲享乐来购买永生,裹住自己来避免死亡,而生命就在我们忙碌于构建人设城堡的时刻与我们渐行渐远。
社会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无能为力构建了第二层防御体系,即构筑一个“英雄”体系让我们相信可以通过参与某项具有长期价值的事情来超越死亡– 征服帝国、建立庙宇、书写宏篇巨著、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等等。这个体系通常被称为文化或传统。
人设是一个人面对世界的脸面,它隐藏着内在的失败。不管人假装自己是什么,他与极度脆弱与消亡只有一线之隔。
很多所谓的“正常人”会自称没有焦虑,天天快乐,其实他们只是生活在某种焦虑遗忘之中,是因为他们树立起一面巨大的抑制之墙来掩藏生与死的问题。到头来,他们只产生垃圾,忘记自己。
宗教作为“永生”项目
如果佛教没有轮回,如果基督教没有死而复生,人们还会去宗教中寻求避难和救赎吗?
上帝是恐慌的国王,是真正的生命渴望。人类对天堂中上帝的向往代表了人类所有的稚嫩和自私:他的无助、恐惧、他对尽可能更多保护和满足的贪婪。
基督教是神秘邪教的竞争者,最后得以胜出,它有一个“治疗者”具有超自然能力,可以死而复生。当哲学超越宗教,它也承接了宗教的中心问题,死亡成了哲学的缪斯 – 从希腊哲学,经过海德格尔直到当代存在主义都是如此。
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本质上来说都是“永生”项目之间的搏斗,亦即圣战。我们战胜恶魔的许多英雄行为经常适得其反,带给世界更多的恶。人类之恶的根源并非人的动物性、并非领地攻击性、并非自私本能,而是由于人类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对死亡的否认、和对英雄形象的热衷。
当人生活在基督教世界,他是巨大整体的一部分,他的英雄主义已经被描绘完毕,没有破绽。他因上帝的创造从不可见的世界来到可见的世界,带着尊严和信仰为上帝尽责,以结婚为责任,以生育为义务,将全部生命贡献给上帝,换来天父对他的认可并将其最终带回不可见的世界,在天堂获得永生。
上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完美的精神客体,是因为他的抽象性。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这种完美。
人设防御体系与自我抑制
战胜焦虑最直接的方式可以总结为:建立人设防御体系和自我抑制。
我们所有的意义都是来自外部,来自我们与他人的交往,这给予我们“自我”或超级自我。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人设防御体系来保护自我。
人会为自己勾刻出一个可以掌控的世界,不假思索、不予质疑地投入其中。他接受一个文化程序,隐藏在某种强大之下,刻苦学习各种技能,为自己建立安全的人设防御体系。这是一个幻觉的没有错误的世界。当他脚踏实地,生活展现为一个预制的迷宫,他不会觉得恐惧。所谓活在当下,往往是因为选择了忘记或忽视。这就是为什么当自我抑制不再有用,当前进的动力忽然消失,人们会突然后背出汗,被恐慌击倒。
人设防御体系支持着一个伟大的幻觉,据此我们便能理解人类的驱动 – 他被从内向外驱使,离开自己、离开自我认知和自我反思,他正是被让他焦虑的那些东西吸引着,将自己推向那些人设的谎言。
同时,一个人还需要全方位抑制,才能克服焦虑。如果他想感到温暖或安全,他必须抑制外部世界的宏大和可能的丰富经验,这样,他才可以克服自己在世界面前的无助感、渺小感、身体和道德的不足、罪恶感、邪恶的打算、死亡意向、仇恨、对自然的恐惧和不解。
自我抑制同样还意味着被社会日常的事情填满,关闭对真实的认知,这样才能感觉满意。自由是危险的,它让人眩晕,太多的可能性会让人发狂,只有繁琐的日常生活才会让人踏实。
生活吞没着我们,我们需要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自己,我们追求享乐,我们追求被社会认可的成功,我们让运气、家庭和爱国主义来主宰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我们在“快乐生活”的歌颂声中日趋平庸,一步步走进死亡的深渊。
蒙田描绘过不堪的农民生活,他们所谓的岁月静好,实际上大都深陷于种种具有疯狂特征的生活方式:连续不断的闲话、虐待、吵闹、抱怨、家庭争吵、自我仇视、迷信、受控于威权,等等。这些足以让他们忘记远方。
当我们离开童年,我们就开始了自我抑制。减少生命的密度、逃离个人成长、指定低水平追求、惧怕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自愿残废、假装愚蠢、貌似谦卑实际上都是针对宏伟的防御。
人的软弱和自欺
让人啼笑皆非又无能为力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谎言来生存,这让我们注定拥有一个不属于我们的生命。
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的重大发现是:精神系统疾病的主要来源是对了解自己的恐惧,人无法剖析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质、命运,惧怕自知和惧怕世界并肩而行。
这种惧怕是防御性的,它保护我们的自敬(self-esteem)、自爱和自尊。我们似乎惧怕那些让我们绝望或让我们感到自卑、软弱、恶毒的知识。我们通过抑制来保护自己理想的形象,我们避免意识上接受不开心或危险的真相。
我们不想承认我们对真相的不忠诚,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生。我们不想承认我们无法独自站立,永远依靠一样东西来实现超越,需要某种思想体系、传统和惯例让我们可以隐入其中,获得支持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见得一定要像上帝般强大或者以强人姿态出现,它可能是某项让人完全投入的行动、激情、对某种游戏的热衷、某类生活方式,就像一个舒适的网让人沉浸并忘记自己。
克尔凯郭尔说,焦虑吸引着我们,成为我们行动的刺激,我们与自己的成长调情,并不忠诚。我们进入一种共生关系来获取保护以减轻焦虑、孤独、无助、空洞感和失落感,但这些关系同样捆绑着我们、奴役着我们,因为它们支持我们自己创造的谎言。所以我们寻求叛逆以获取自由,但嘲讽的是,我们不加批评地叛逆,与我们自己的盔甲搏斗,挑战自己,殊不知这样获取的也只是“二手”自由。
我们所谓的挑战自己,无非是通过提高极限来寻求压力,这种挑战针对的是“绝望的屏障”而不是绝望本身。赛车、股市、公司级别、马拉松、登山无不是如此。
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丰富人生的二手特征:甚至在激情中,我们也无非是小孩子在玩弄着代表真实的玩具。甚至当这些玩具毁灭,带走我们的生命,我们还自我安慰着,以为这些是真实世界而不是幻想的矩阵。
人们的非本真,在于他们不属于自己,不是他们本人,不是从自我出发,不是凝视真实。他们是单向的人,完全倾注于社会的虚构游戏之中,无法超越其社会制约,不能独立思考。他们是被动的文化人,是文化建构的奴隶,是被文化限制的庸人;他们从信用卡的颜色中找感觉,以为开着保时捷就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人性结构的最深层是死亡或死亡恐惧层,这是我们真实而基本的动物焦虑。到达这一层,才能找到我们的“本真自我” – 我们真实是什么。这里没有耻辱、没有包装、没有针对恐惧的防御。
在《黑客帝国》中,莫斐斯让尼奥选择红药丸和蓝药丸,前者可以让他看到残酷的真实,后者可以让他回到过去生活舒适的谎言。尼奥吞下了红药丸,眼前的世界瞬间崩溃,当他赤裸着在充满液体的玻璃罐中重新醒来,才看到真实的自己。要想看到真实,一个人必须死去,然后重生。
(个人读书笔记,内容几乎全部摘译自Ernest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本书曾获1974年普利策奖。)
2020.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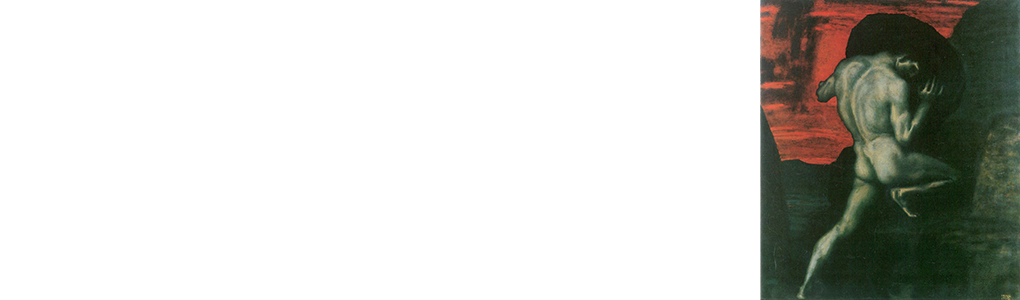
《那挥之不去的焦虑,那未曾活过的人生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1)》有2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