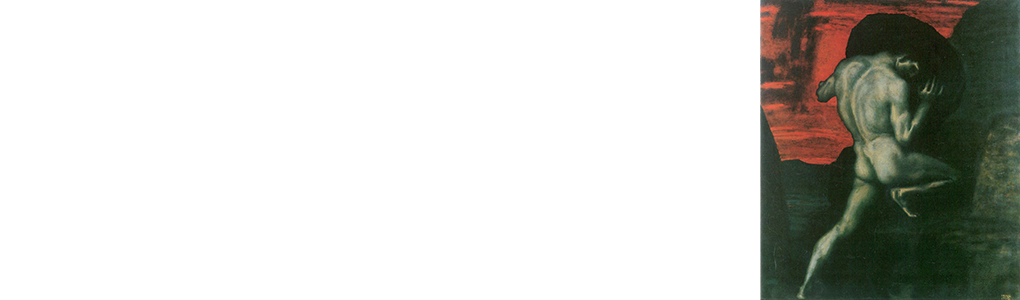1
那个隆冬的夜一定很黑,平原上的村庄万籁俱静。微微驼背的中年汉子在妻子的叹息声中,在几个孩子不解的注视中,披衣走出低矮的土坯房,从院里推出那辆上面摆满家什物件的木轮小车,弯着腰,悄悄穿过他熟悉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来到村子中央一处大瓦房旁边的农家小院。他看看四周没有动静,轻轻叩门。
开门的是一个瘦弱的小脚少妇,手里拿着煤油灯。面对她惊恐的眼神,中年汉子示意她不要说话,轻轻把车子推进小院,在沉默中将车上所有的物件卸下来,然后沉默着离去。
中年汉子是我的姥爷,贫农,抗日时期堡垒户的户主,村里第一个共产党员。那个小脚少妇是地主的小老婆,地主已经携家逃走,只留下她孤零零一个人,被村委会赶出了原来的宅院。
很多年后,母亲对我说,本来姥爷分到了大瓦房,但他坚持不要,说住那样的房子不踏实,日后总归是要还的;于是,村里只好把地主家的家具摆设缎被之类分给他,他说服姥姥,趁黑夜全部送还给了人家。
我在母亲家乡那个有上千人的村子读完小学,记忆中的姥爷是一个沉默的行动迟缓的老人。我很为他的贫农成分而自豪,也很失望于每当学校组织贫下中农来忆苦思甜,姥爷从不出面。我曾经问他给地主当长工时是否被欺负,他却说地主全家都很厚道;我也缠着他讲述抗日被鬼子抓走坐老虎凳、又被组织营救的往事,他总是摇头笑笑,一言不发。
大人们说起姥爷,总为他惋惜:组织曾动员他随部队南下,被他以孩子太多为由婉拒;抗日时被他救过的游击队长后来在北京做大官,邀请他赴京,他也从没接受。不懂事的我看着那个越来越驼但又总是慢吞吞操劳着的小老头,觉得他有些窝囊。
等我自己已是中年,见过些所谓的世面,读过几本没用的书,姥爷的形象在我心中反而高大起来。我觉得,姥爷很像那种会冒着风险,把犹太人藏在家里的极少数的德国人;如果他是军人,当面对赤手空拳的百姓,他肯定会把枪口抬高一寸。
姥爷活到八十多岁,和姥姥养大六个孩子。我的大舅后来考上空军学校,做了军官,我的大姨嫁给抗美援朝的英雄。姥爷供母亲读到初中毕业,成为村子有史以来第一个“吃商品粮”的女教师。
我有时后悔,小的时候应该多跟姥爷混。那样的话,长大后可能会少做很多蠢事。
2
我姥爷不识字。依稀记得村里老人说,姥爷小的时候,也曾跟着乡下先生读过几天书。不过他很捣蛋,声言: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念。
奥斯卡颁奖,女导演致辞,也提到人之初、性本善。她说这几个字一直影响着她,她总能从身边人那里看到善的一面。她要把自己的获奖,献给那些有勇气和信念,不管如何艰难,也能坚持自己善良并以善待人的人。
以我有限的育儿经验,我很怀疑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说法。至少从折腾大人这个角度讲,刚出生的小孩子没显露出丝毫善意。进化论告诉我们,人一出生,首先体现的是自私的动物天性。当然,自私并不是恶,正如利他未必一定是善。我倾向于认为,人类本性中,善与恶并存。我们的内心,既有善良的天使,也有邪恶的魔鬼。善恶不在于思,而在于行。
“行动”本身善恶的界限常令人感到迷惑。我欣赏的近代大作家,如塞林格、米勒、克鲁亚克和纳博科夫,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以第一人称来讲述年轻时寻找性交易的经历。他们并非津津乐道,而是在以个人的经历透析人性最底层的原始欲望。
寻求性交易属于“私德”范畴,不难想象,很多人都做,只是通常做了都不会说,因为这毕竟“不体面”。不久前我却遇到例外:若干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邀我喝酒,我以为与多年前的有志青年相会,总免不了指点江山。没想到两个半小时的话题,全都是有关性交易时间长短、成本高低和质量优劣。在为朋友们身体健康感到欣喜之余,我也很震惊于把这事拿上台面的坦诚。不过我很快意识到:一起谋坏事、干坏事、聊坏事恰恰是中式友谊的核心。
再重申一下,我不是道德学家,不想评判性交易本身的是非。这次聚会的话题让我联想到,周围实际到处都是对各种“不体面”的集体性热情和参与。比如,你注视一下酒局上的杯盏交错,寒暄、溜须拍马背后那些互相利用的动机尽人皆知,但每个人都很享受这种气氛;你再想想有多少场合,谁都知道所有的发言都在撒谎,但每个人都在正襟危坐着鼓掌;在多少公司里,老板完全无视下属尊严,破口大骂,而所有参与者都装孙子默不作声。
表面看上去,参与者都只是无伤大雅地应酬着、顾全大局地顺从着、循规蹈矩地勤奋着,但这种群体对不体面、小“丑恶”或坏习俗的共同不在乎,意味着基础价值体系的崩塌。当丑态毕露成为情感的纽带,人们便会忘记高贵的真正含义;当假话开始发自肺腑,真相便无处可寻;当套路成为人生的智慧,你就再也看不到人性的光辉;当察言观色和话术被誉为情商,正直和忠诚就会消失。汉娜-阿伦特曾提出过Banality of evil,人们通常将此译成平庸之恶,但她的本意其实是恶的平庸。恶,没有什么深度,恶的开始,往往就是细微之处的所谓人之常情。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曾经论述,孤立的个体会有很多恶劣的动机或打算,即使受到诱惑,他也能权衡,并且有可能控制住自己。但个人一旦进入美丑不分、善恶不辨、黑白不明的群体,个人就不再为其言行承担责任,每个人都会尽情暴露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证人消失,全体成为共谋,这就出现了“集体性趋恶”。
在一种随处可见的“集体性趋恶”状态下,人们更习惯的将是以恶交友,更崇尚的是因恶而赢,以共同的恶来获得安全感,既不必谴责,也无需忏悔。只需要一句”都一样、没办法“,所有的同流合污于是便都成了天经地义,文明赖以形成所需要的道德力量从而烟消云散。
当人们不再顾及体面,当仁慈善良被看作愚蠢,当说谎成为生存的必须,可以肯定,人类本性中邪恶的魔鬼已开始大行其道,个体恶意将在群体的引导和纵容下无限放大。
3
毋庸置疑,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舒适和平的时代。尽管过去一年多的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的伤痛,尽管媒体上经常充斥着凶杀与悲苦的新闻,尽管预言家们总喜欢以制造对未来的焦虑来获取关注,尽管人们经常会对远逝的岁月给予浪漫的想象,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裕、方便、安全。
曾几何时,暴力和死亡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但过去七十多年,人类社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文明世界几千年的历史趋势也表明,不仅军事战争的频率在下降,几乎所有形式的对生命造成威胁的人际暴力都在减少。我们已经目睹甚至仍然可以期待越来越少的谋杀、屠杀、抢劫、刑罚、以及对弱者的欺凌。
为什么能够这样?斯蒂文-平克总结说,这是因为人类越来越被我们本性中更好的天使指引着。天使是同理心,让人们能设身处地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天使是自我控制能力,让人们能基于预知的结果而行动;天使是道德感,让人们能明白是非;天使是理性,让人们不再因蛊惑而疯狂。
平克是学者中少见的乐观主义者,他进一步总结,现代民族国家对武力的克制,商业行为的扩大与技术进步,女性地位的上升,文化与见识的提高,以及人类事务的理性化,共同形成合力,抑制了人性中导致暴力的五种“邪恶”心理系统,即:捕食或工具性暴力冲动、支配欲、复仇心、虐待欲以及意识形态狂热。
当社会达到一定文明程度后,理性是人类得以抑制暴力的最大希望。集体性趋善而非趋恶,才是终极的致赢之路。如果某个群体丧失了理性与逻辑,丧失了道德感和同理心,又膨胀到难以自我控制的地步,最终一定会灾难临头,惹火烧身。
囚徒困境是一个简单的博弈游戏。两个在监狱中的囚徒,有共同犯罪嫌疑。囚徒们被分开审讯,各自被劝诱背叛同伴,将所有罪行栽赃给对方。如果甲方所有罪过推给乙方,而乙方保持沉默,那么乙方将接受重罚,而栽赃的甲方则被无罪释放,享受背叛的红利。如果两人互相背叛,便都将获罪,但会因供认得到判罚,这是互相背叛的“坏处”。如果两人选择不与警方合作,闭口不言,也会因证据不足获得轻判,得到互相合作的“好处”。因为担心对方的背叛,假设两人都以自私动机来选择,最终都会选择背叛,从而受到惩罚。
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讨论了囚徒困境里双方如果持续重复博弈,采取哪种策略可以最终赢出。在重复博弈中,实验者征集了几十种不同的策略,同时加入随机性策略。他们将这些策略翻译成计算机语言,让每一个策略都轮流与其它策略进行反复博弈。出乎意料的是,最后胜出的策略最简单、看上去也最不聪明。
这个策略是善良与宽容的组合。“善良”是指实施者从不率先背叛,但假如对方在上轮背叛,那么他接下来会立即报复,针锋相对,毫不手软。“宽容”是指实施者只有短期记忆,虽然他采取报复行为,但也很快忘记对手的劣迹。这种“一报还一报”的策略鼓励实施者勇敢地向对方率先发出善意,而不是执着于判断对方做什么。如果发现对方并没有对善意作出回应,则立即改变行动,但这种改变只根据对方上一轮的反应而定。
善良、宽容但同时“针锋相对”的策略,在很多轮中可能是吃亏的,持续重复之后最终胜出的结果也未必大幅超过其它策略,同时还会不断受到其它恶意策略组合的攻击。科学家的推理是,相对于恶意的“背叛”策略,从善意出发的“针锋相对“更容易获得个体聚合,从而超越决胜点。
人类在宇宙中,亦如囚徒。道金斯说:“即使我们都由自私的基因掌舵,好人终有好报“。囚徒困境是一个非零和博弈,带着善意,人们可以一起笑到最后。这个结论让我对人类的未来谨慎乐观。爱拼未必能赢,最具智慧的人们一定不会选择邪恶,他们一定能聚在一起,共同让本性中更好的天使来指引着,他们一定会选择最简单、最不聪明的策略:善良、宽容,针锋相对。
大道至简,个体如何选择,看上去很难,其实也很简单。
20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