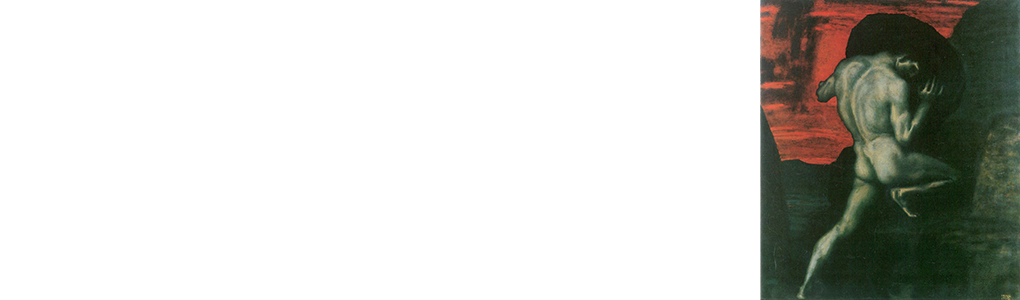二〇一八年的秋天,我和JZ爵士的创始人老任在咖啡馆闲聊,他突然说:老劳你写的东西我喜欢,找几段发在我们爵士邮报上吧!
老任提到的我写的东西,不过是我胡乱发在朋友圈的稍长一些的随感。我不觉得那算是文章,但有人喜欢总归令人开心。于是笑笑对老任说,好吧,你随便发。
那年圣诞节前,爵士邮报的编辑发来一个链接,正是下面这篇《我的咖啡馆》,短短只有一千多字,成了我的处女作。从那开始,我陆续为邮报写过几篇。后来因为想写的东西和艺术生活相差太远,于是开设了自己的公众号。第三个月的时候,有篇文章的阅读量超过了三十万,关注者猛增。女儿对我说,主要是你文章的题目比较长。
《荒诞主义咖啡》被消灭之后,伊璐又帮我开了现在的《局外人咖啡》。两年下来,写了几十万字,但愿意拿出来给人看的内容却很少。我有时会想,写这些东西,有何意义?我到底改变了什么呢?
显然,我并没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人间依然是日复一日渗进每一个缝隙的喧嚣繁杂,每天都有愤怒,每天都有灾难。我也并未能如愿帮到我生活中重要的人,很多时候你掏心掏肺,很多时候你以为亲近无间,两颗心的距离却远过万水千山。聊以欣慰的是,在空茫虚拟的空间里,我知道的确还有少许同样挣扎着的灵魂。
古往今来,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往往是那些傲慢地以为可以改变世界的人;许多自以为高尚的个人牺牲,往往是为并非真正爱着的人们去战斗,实在无谓,实在不值。一个人能改变和拯救的,最终可能只有他自己。也许,这应该是写作终极的意义。
Lex Fridman在他的访谈节目中,经常向那些卓越的科学家和作家提问:你是否怕死?最能触动到我的回答是:当然怕死,但主要是怕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做完自己能做的事;而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再也不能被人记起。我没有想过名垂千古,但内心的确有个小小的奢望:留下一点东西,留下一点只属于我的东西,在遥远的未来,我已离去,而我牵挂的人或许看到这些东西,就像抚摸着我的手臂。
那么,我该留下什么东西呢?去年疫情期间,我在短文中写到的那个咖啡馆关闭,夜里从门前路过,里面一片漆黑。不久之后,那里可能会有新的装修,开出某个新店,抹去过去所有的痕迹,有谁还会记起那里曾经流逝的生命、曾经发生的故事?那里真的有过生命、有过故事吗?关于那个咖啡馆,关于我在那里度过的那些下午,唯一能留下来的也许就是我写的那几行字。如果再看人类历史,除了浓缩于艺术、符号和文字的思想,最后还有什么能战胜时光、暴力和无数天灾人祸的摧残?
而以我浅疏的才学,又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我不想批评或揭露,也学不会颂扬。大道至简,公理昭然若揭,是非曲直清晰可见,人们只是任凭内心的恶魔信马由缰。我愿意和能做的,或许只是在到处都是谎言的时刻说几句人话,不让自己已经长大的孩子难为情,不让我敬仰的人们耻笑,而自己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看,也无需任何修改。还有,或许我可从自己半生的挣扎中,清点出片许黑暗中能闪亮的燃料,分享给旅程中让我在意的那些人们。
此刻,是周六的下午,我坐在古北一个咖啡馆露天的座位上胡思乱想。刚才不久,我在这里和年轻的外甥喝过咖啡,我们聊了很多:职业、金钱、权力、爱情、人生的种种枷锁,那是两代人之间朋友般坦诚的交谈。对呀,即便不必重述细节,但何不记下今天这段很认真也很轻松的时光。
我刚搬到上海的时候,外甥只有十来岁。那时我肯定不是个好舅舅,经常搞点恶作剧逗他,弄得他很愤怒,不愿理我。后来他去美国读高中,暑假回来一下成了个大小伙子,我开始把他当成大人,从此发现我们有越来越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如今,他大学毕业回上海做视觉艺术已经好几年,慢慢悠悠,长发飘飘,我很欣赏他的澄澈,他也认可我的努力。能和自己的外甥做朋友,实在是平淡人生的一大幸事。
世间轻飘飘的快乐随处可寻,可人生又能有多少值得记下来的认真、厚实而温情的回忆呢?今天,我独自坐在附近这家新找到的咖啡馆,想着刚才和外甥的对话。他是个因多思和友善而显得过于严肃的青年,有很多困惑,他在寻找,寻找自己,寻找梦想,寻找世界的真实,寻找那些能为人生带来复利和累加的体验。
眼前的一切年复一年地生机勃勃:右边望去,初夏的阳光此时依然耀眼;转头透过浓密的树叶远眺,大上海天空湛蓝;咖啡馆门前灌木的顶部,小虫飞舞,新绿葱葱。我和外甥说起一百年前,斯泰因曾在巴黎烟雾弥漫的咖啡馆里对海明威说:你们是迷失的一代!七十年前,克鲁亚克和金斯堡们瘫坐在丹佛热腾腾的爵士酒吧里,也曾自嘲是垮掉的一代,疲惫不堪。
被指责迷失时,海明威们只有三十来岁;自嘲为垮掉时,金斯堡们也正值壮年。此后几十年里,他们各自既没有停止寻找,也没有结束战斗。等他们终于有一天选择躺倒的时候,大地悲歌、群星璀璨,他们再无需站起,因为他们已没有遗憾。
回想自己,在外甥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迷失,那是因为没有去寻找;也没有觉得无力,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去寻找属于我的战斗。照此说来,他是幸运的,他不想浑浑噩噩,更不会随波逐流。我帮他做不了什么,只能默默为他鼓劲:可以迷失,可以疲惫,跌倒再爬起来,走错就重新来过,无论如何,只要有梦,就不会躺下。
外甥要去徐家汇和同伴聚会,与我道别。看着阳光下他年轻的背影,我有些怅然。想着这两年半的经历,想到最初写过的那个咖啡馆,想想未来,我知道,有种感觉似曾相识,会不断轰然而至,那是迷失,是疲惫,也是无尽的悲哀。有个苍老的声音在嘲笑:年轻人都在躺平,你已是晓风残月,不要再做梦了吧。
其实这也未必。新找到的咖啡馆名叫“简单的梦”,很应承我此刻的心境。年轻的梦大都是凌乱而又荒诞的,人们醒来往往什么都记不住。我不应该去羡慕年轻人,更不必自怜自哀。毕竟,我终于找到一个简单的梦,一个能天天记在心里的梦。
202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