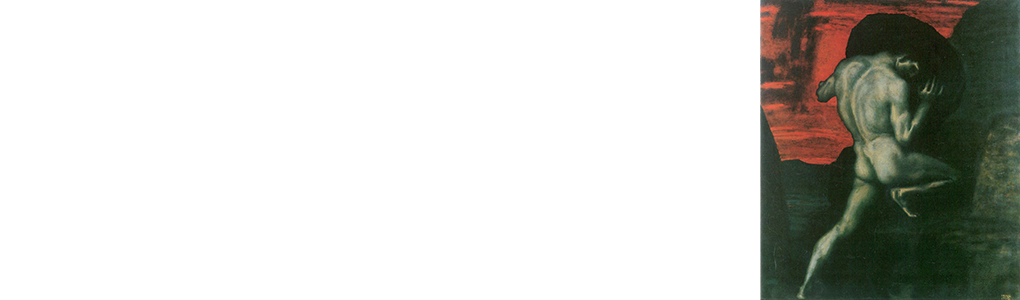1
钱塘江临近入海的北岸一线,有个地方叫大缺口。站在这里的堤岸上,前方的江面如同一个巨大的喇叭口。每当涨潮时分,汹涌的海潮从南向北,由宽及窄,层层相叠,撞向大缺口的堤岸,然后在此处愤怒地转头,滚滚向西而去,如素练横江,奔向古今千年以观潮闻名的海宁盐官。
大缺口北面的小镇,名叫袁花。1951年4月的某个清晨,田野里油菜花金黄一片,镇上公安人员从临时监狱里拉出54岁的乡绅查树勋,草草验明正身之后,不赏酒饭,将其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奔向镇上小学。抵达后,查树勋和另外三人被摁着跪在操场上,脑后枪声响起,四人倒地而亡。
在此几年之前,查树勋曾经在他洒下一滩紫血的这个操场上给孩子们讲话。作为当地世代名流,他一生诸多善事义举,重建这所小学则最令他自豪。毕竟,才华已露、有望继承渊源家学的爱子查良镛,当年就是从这所小学毕业。
此时,文艺青年查良镛已经远遁香港,对于父亲的被枪毙,他只能面向北方,以痛哭宣泄悲愤。1955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写作《书剑恩仇录》,其最初场景即为自己的家乡浙江海宁。此后,金庸陆续写下十几部武侠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社会享誉斐然的大侠,他自己在小说中也塑造过许多失去父亲的英雄,要么一生执意寻父,要么立誓报杀父之仇。
父亲被枪毙三十年之后,查良镛已是香港名流,应邀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受到邓小平接见。会谈中,邓公主动谈起查父被杀之事,劝导查良镛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查连连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回港之后,查良镛立即寄给邓公一套小说全集。从此,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迅速风靡大江南北。神州一代学子精英,无不摩拳擦掌,做起壮志凌云、快意恩仇的江湖梦。
2
大学时代,我也读过几套武侠,可越读越绝望。那时只有二十来岁,看到能让女生倾心相许的人物如乔峰、令狐冲、张无忌、郭靖之流,个个武功高强、豪情满怀,像我这般的文弱书生则毫无出路,从此难免对江湖心生恐惧。
江湖,River and Lake, 听上去清俊浪漫。和众多汉语概念一样,你无法给它下定义,但它在诗书和交谈中又无处不在,不属于“博大精深“,更像是 “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金庸曾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照此说法,江湖的空间边界可无限延伸,家之外、国之内,均为江湖。离开了家,只要你在华人世界,理论上讲,你已经身在江湖。
江湖与恩怨密不可分,而恩怨正负相等,只是零和游戏。所以江湖中必定是有输有赢,有成有败,有火并但没有购并,江湖不相信价值创造。
人们可以唱,让世界充满爱;好像没人唱过,让江湖充满爱。江湖刀光剑影,打打杀杀,只有英雄才配享受血色浪漫,你何时见过喽罗们儿女情长?
关于江湖,最多的说法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何为己?己就是我,江湖里不允许有自我,除了老大的任性,它严禁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江湖只讲规矩,不讲法律;只需忠诚,不要真诚;只求侠义,不求正义。你可以自称微风清扬,你可以意淫逍遥自在。一旦你忘记规矩,便将有口难辨,成为众矢之的。凡有清高,必是异己。
江湖需要投名状,无论是情谊的巩固,还是忠诚的建立,总要基于一起干些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把柄,而所有的心照不宣都意味着深不见底。
昔日的江湖有帮,人们在帮里寻求安全;如今的世界有圈,人们在圈里找到存在。无论是帮还是圈,都只是共同利益的维护,而不是信仰的捍卫。帮里有帮主,圈内有大哥,江湖生涯的成败只取决于能否做老大或是否能跟对老大。
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咏道: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可见,江湖基本上是一个吃青春饭的地方,时光急,老的快。这里不可能有慢生活,既不安稳,也不静好。无论大碗喝酒,还是大口吃肉,都只是将粗鲁当成豪放,背后是有今日没明朝的深深恐惧。
江湖故事中,英雄最好的归宿往往是看透一切,携佳人远走天涯,而这毕竟只是写故事者自己都不相信的希冀。现实中,有志向者进入江湖是天经地义,是人生的默认配置,在你有可能对其发出质问之前,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江湖有一种自我和谐和均衡的逻辑,它既能满足虚荣心,又能解除孤独感,以至于每个人不管得意还是委屈,都愿意为之筑堤开渠。所以,江湖人士只会抱怨但不会逃离,因为只要逃离便意味着既得利益和人生意义的双重失去。
3
我对武侠小说没有太多兴趣,对金庸生平的少许兴趣仅仅是由于多年前曾在他的家乡海宁打工。那时,每当我开车经过他出生的袁花镇,看到指向他旧宅的旅游路标,总是不免疑问,作为华人世界最著名的作家,曾塑造出那么多的英雄豪杰,对他自己父亲的被杀,为啥却没有写下任何文字?
据说,当年金庸写《书剑恩仇录》的初衷,是为给自己创办的《明报》扩大读者群,解决短期财务危机。可见,他的小说创作首先还是流量的考虑,而非直抒胸怀,不吐不快。我一向认为,艺术创作可以分成三个境界,即用手、用脑还是用灵魂。金庸写下十几部几百万字的武侠小说,用到的只是手和大脑。他娴熟地把都市青年的浪漫幻想和大众最为自豪的中华国粹,融入进似是而非的历史背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成人童话,其技巧与才华确实无人能及。这也难怪,中国文学史上,在世便能如金庸一样功成名就、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地驰骋于政、商、文三界,再无他人。
但金庸有其清醒,最终毕竟还是委婉地用个人行为和文学的双重隐喻展示了灵魂一隅:写下《鹿鼎记》之后他毅然封笔,此后四十多年中再未创作武侠。在《鹿鼎记》中,他塑造出韦小宝这样一个厚黑学最高段位级的“反英雄”,也算找到些艺术创作最不该缺失的诚实。
八十年代后,金庸曾多次被政府热情邀请回到浙江,他的出生地祖宅被翻修成纪念馆,他家乡的道路改成了与他和武侠有关的名字。家国厚重,盛情难却,他到过杭州,到过嘉兴,到过海宁,但他从没回过袁花,从未踏上他家乡的土地,而且一直以不近人情的执拗拒绝见到他那仍然留在祖籍的胞弟。
我只能猜想,金庸到了海宁而不去袁花,甚至拒绝与几十年未见的弟弟重逢,或许是想到了他自己小学时代的那个操场。对于父亲的死,这是他做到的所有的表示。当然,人们可以引用他的名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英雄岂能纠结于自家那点小事。但假如这样,又何以谈及“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其实,千年来文人所谓的心怀天下,依然不过是魂系江湖。侠之大者,最懂江湖规矩也。
十几年前,金庸偕夫人回海宁,先是为金庸书院奠基,后又在各级领导陪同下登上盐官的观潮亭。据报道,那天金庸不时拿起望远镜,热切等待大潮的到来。最后,他终于远远看到一道白线化作“雪岭”,但没听到轰鸣。领导们解释说:风太大,风太大。金庸含笑称是。
当年在海宁,曾趁月明星稀去袁花镇南的大缺口观夜潮。翻过高处的防护堤,来到距离江面最近的平台,我和同伴喝着啤酒,等大潮的到来。午夜时分,隐约听到远方沉闷的响声,良久之后,响声才慢慢轰隆,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如滚滚雷鸣。月光下望去,渐渐逼近的白线并不迅猛,但骤然之间,白浪下巨大的水墙已扑向堤岸,正如金庸所写:“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
惊吓之中,我们屁滚尿流跑回防护堤上,等大潮向西而去,才敢回到堤下平台。这时,江面已经涨起,浊浪翻卷,地上,啤酒还在,猪蹄也在。
海潮汹涌,真实而壮美,只要把握距离,近观并无危险;而江湖如梦如幻,波光粼粼的浅水之下,深厚的淤泥温柔细软,它从不拒绝任何人,你随时都可以踏进,甚至有时可以脱身,但你永远无法逃离。
202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