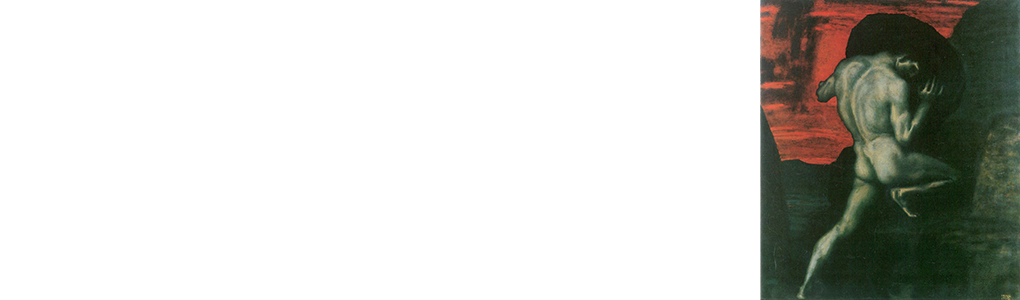1
死去的诗人其实是进贤路上一个酒吧的名字。酒吧灰色外墙上,有一块形状古怪的金属招牌。射灯从背后照过来,招牌就像一块带着黄色光晕的陨石,从墙里飞出,没人能注意到上面还有Dead Poets几个字。我和于君进去后,被侍应生带到吧台角落的空位。右边有对情侣,隔着他们,吧台边坐着两个相谈甚欢的姑娘。我只能看到其中一个女孩白皙精致的面孔,青春洋溢,神采飞扬。
进贤路是一条短短的小街,东面连着茂名南路,西面和陕西南路相接。很多年前,但凡有朋友到上海,我都会带着他或她先到进贤路上沪上阿姨掌柜的店里吃本帮菜,然后去当时还在复兴西路四十六号的JZ俱乐部听爵士。那几家装饰简陋的小店生意红火,客人常不得不拼桌。每家门外的马路牙子上都摆着一排塑料凳,夏日炎热的傍晚,总有不少年轻男女在那里等位。
于君算是我多年的朋友,当年我曾带他来过进贤路。估计这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这次来上海,他特意住在了老锦江。晚饭的时候他发微信给我,以前那些小店,现在只剩下一两家。不过有个新开的酒吧好像不错,叫Dead Poets,他想进去喝一杯,却被告知没有空位。我对他说,可能是你显得太老,人家不想让你进去。
后来,我们还是约在四年前搬到巨鹿路的JZ俱乐部,我和那的老板任宇清很熟。不巧这晚老任不在,他是个贝斯手,几天前和李泉、老黄等人去了深圳演出。JZ每晚都安排两个乐队,当晚的爵士大乐队演奏完大半,等性感的女歌手下场,换上一个戴礼帽的男人,已是临近午夜。于君和我走出JZ,才发现此刻同乐坊广场里,每家酒吧依然还是人声鼎沸。上海的夜,还很长。
于君说,我们再去Dead Poets碰碰运气吧,都这点儿了,也许能进去。
2
于君大学毕业于清华,后来去斯坦福读金融,在美国投行工作几年后回国,先后在几个著名的上市公司做高管。五六年前,他行使完最后一笔股票期权,卖掉北京的房子,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去了荷兰。在阿姆斯特丹郊外的蓝天绿野,孩子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于君夫妇热爱艺术和旅行,他们在国外的日子雅致、丰富、忙碌而又清静。只是双方在国内的老人如今需要照顾,他们也想让孩子们学好中文,于是疫情之前,全家又搬回北京。没想到,这是于君烦恼和焦虑的开始。
于君是七零后,或许正属于典型的中年危机症候群。在他自己看来,如今烦恼的理由充分而显然:六年前他把北京的两套房子卖掉,这些年投资回报并不好,现在回来,当年那些钱只能买回一套;几年不见,曾经的同事或同学在国内的事业风生水起,别人的身价都翻了若干倍,他还是在吃老本;孩子们读国际学校花费很大,而他因为年龄关系能选择的工作机会却乏善可陈。
我比于君大几岁,十几年前就不再全职工作。于君这种切实的失败感我也有过,至今仍然会时不时袭来。今晚,JZ舞台上红色的厚丝绒背景幕布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展现着一种绚丽的深沉;来自纽约的歌手身着低胸黑裙,性感艳丽,在大乐队的伴奏下演唱着百年前黄金时代的经典,时而低吟,时而昂奋。一曲完毕,掌声中我将目光从舞台上移到我身边的于君。这老弟是个公认的美男子,身材高大,目光坚毅,当年迷倒过多少好姑娘。看到黯淡的灯光下他依然棱角分明的脸上也开始蒙上一层沧桑的雾,我心中竟有一丝恶劣的快意,你小子也有今天。
3
死亡诗人酒吧的酒单精巧别致,和酒价很相配。每款店配特色鸡尾酒的开头都有DP两个字母,这是Dead Poets的缩写。当我和于君各自选酒的时候,侍应生带过来一个姑娘,安排坐在吧台直角的另一边,正好是我的左侧。这是酒吧剩下的最后一个座位。
虽然已是秋天,上海今晚并无寒意。姑娘穿着正式夜宴上才能见到的白色裙装,手上的戒指大得有点夸张,不过看式样更像是文艺的低调时尚。精心修饰过的妆容优雅而不失自然,柔黑的短发微微后卷,衬出两个细长而轻巧的铂金耳坠,使她乳白色的小脸显得更加俏丽生动。于君和我应该一样惊喜,身边会骤然出现这么一位佳人。
酒吧电子乐的音量恰到好处,低沉的贝斯轰动令人心神不宁。如果两人交头接耳,旁边的人不会听到。于君凑近我,左右看了一下,悄声问我:“吧台上这些女孩,不是那什么的吧?”
我能理解于君的好奇心。二十来年前我们一起在深圳工作,深夜去酒吧碰到这种状况,他的这种猜测基本可以确定,女孩子会采取主动。而这里是2020年的大上海,他想得太多。这些年,我自己除了偶尔去JZ,很少再去泡吧。但我那在国外读大学的宝贝女儿回到上海,也会约别的女孩一起去酒吧。“亏得你还在阿姆呆过,怎么越来越土?”我对于君说。酒吧里大都是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到处欢声笑语。只有吧台边,坐着我们两个脑门子上写着失意的老男人。今晚,于君明显比我猥琐。
我和于君点好酒,他又感叹:“这些女孩子虽然打扮得很高雅,但看不出有什么Substance。”不出所料,和我前些年很像,于君面对青春,也开始了酸溜溜的油腻。Come on,老男人们满脑袋里都是与功利和肉体相关的烦恼、惆怅或自鸣得意,那些也能叫内涵?
4
也许是因为此前在JZ喝过几杯,也许只是想在于君面前显摆一下勇气尚存,我转头面向左边的女孩。“不好意思,姑娘,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女孩一怔,本能的警觉让她身体微微后倾,正要举手拒绝,我注视着她,坚定而真诚:“如果能请你喝一杯,我会觉得很荣幸。”
她看到了我的执着,很给我面子,不自然地点头致谢,我也放下心来。三十来岁的时候,我单身在当时还被称为汉城的韩国首尔工作,每个周末都要去延世大学附近的酒吧,而去酒吧只有一个目的。不过,那时我都是和当英语老师的美国人迈克尔一起,打招呼破冰这件事都由他来完成。韩国女生对外国人很友好,我有时还会想起那个名叫伍德斯托克的只供扎啤的酒吧。回国之后最初很多年里,我只在KTV里和女人喝过酒,尘世荒唐,不值回望。
很快,于君也加入了我和女孩的交谈。她叫小然,宁波人,六年从杭州来上海工作,现在一家上市集团的投资部做投后管理。于君和我过去的工作都和投资有点关联,所以和小然不缺共同话题。小然说,她们公司在浙江起家,上市后集团总部搬到上海,在国内外投资了很多项目。作为投后管理的负责人,她经常出差,哪怕是疫情期间,她也不得不去美国,曾经为此隔离过两个十四天。
小然大方开朗,身材娇小细柔,谈吐间流露着一种少见的果敢。
5
我平素不太愿意和年轻人聊天,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人总是克制不住要自夸、说教或者怀旧。这个晚上,我有些兴奋,不免犯忌对小然和于君说起一些往事。
我读大学是在八十年代,当时很多人都有一本上下两册的新诗潮,里面汇集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优秀年轻诗人的代表作。毕业前夕,我认识了在《十月》当编辑的何拓宇和他的同学诗人骆一禾,他们成了我崇拜的偶像和敬爱的大哥。若干年后,我在巴黎巧遇新诗潮的编者老M,一个身材矮小貌不出众的安徽人。也许是因为我身边的女朋友有点漂亮,老M竟然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我惊奇地发现,他和拓宇、一禾是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
一禾在三十年前就已离开人世,拓宇也在十几年前驾鹤西去。和老M巴黎一面,再无联系。此前一天,我刚从微信某个群里看到,老M刚刚因病去世。原来,九十年代后期,他曾因精神失常,流浪巴黎街头很多年,贫病交加,五年前经历了很多周折,才被弟弟妹妹接回到安徽老家。
在这个温润的秋夜,在酒精和音乐的弥漫之中,年轻的生命肆意盎然。望着沉醉在橙红色灯影里那些欢乐的面孔,我不太知趣地讲起这三个死去的北大诗人,想起他们曾经年轻而充满希望和热情的音容。我举起酒杯,对小然和于君说,既然这个酒吧叫Dead Poets,那咱们一起为死去的诗人喝一杯吧。
场面一下子变得很尴尬,小然不知该说啥。我似乎听到耳边于君对小然说:没事,我这哥们儿是文人,有时喝多了就会这样。
6
于君今晚的好奇心特别强烈,和小然聊熟后,他抛出了那个困惑了他很久的问题:“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怎么大半夜还会一个人来酒吧?”
小然回答:“我今晚刚参加完朋友的生日聚会,回到家快要进门,听到父母还在客厅说话。我不想进门面对他们,所以就下楼走到这个酒吧喝一杯,等他们睡了再回去。”
听她这么说,我禁不住问道:“那容我冒昧问一下,是不是你父母在催着你赶紧结婚?“
小然点头,说这件事让她很烦,现在和父母的关系有些紧张。我算过,小然六年前来上海,如果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应该差不多二十二岁,现在大约二十八。
接下来,我好像说了诸如现在好多父母都这样、婚姻与否都不重要之类的话,结果被小然很不客气地打断,她说:“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吧。“
沉默。我意识到,我已经喝得有点多。
7
环顾四周,不觉之间,很多座位都空了下来。小然从座位旁拿起她黑色小巧的香奈儿手包,也准备离开。我结完账,三人走出店门,于君善意地提出顺路送小然,被婉言谢绝:“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家就在这旁边,我自己走回去就行,几步路就到。”
我们没有坚持,留在原地,目送她娇小的背影走向路尽头的茂名公馆,细细的足有十几公分的高跟敲在湿滑的路面,发出转瞬即逝的声响。夜空中飘忽起凉意,贴近路灯的地方彷佛能看到些许晃动的雨丝,梧桐树上那些饱经风雨摧残的树叶,有几片悄然落在地上。
于君觉得有些遗憾:“跟她聊得挺投机,咱们都应该加个微信啊!”其实,我也想过这一点,而且深信如果提议的话,她应该不至于拒绝。但后来我想:何必呢,就这样一起喝杯酒,就此别过,互道珍重,还不至于让自己丢掉老脸。
于君这次周末来上海,是为了下周去某上市公司面试,那家公司的老板籍贯正好是宁波。我跟他开玩笑说:这姑娘来上海六年,就在上市集团负责投后,和父母一起住茂名公馆,说不定她就是你未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女儿。
8
那晚我应该还调侃过清华没有诗人,以及像于君这样的理工男不懂诗。这是因为当我提到北大那几个死去的诗人的时候,于君说:写诗是一种obsolete form of art,即早已过时的艺术形式。
我自己本科也是理工男,从没写过诗,年轻的时候虽然买过很多现代诗集,但也只是附庸风雅而非真正欣赏。近几年,从吉姆-莫里森冷漠的歌声中,从帕蒂-史密斯古老的琴弦里,凝视着巴斯奎亚特那看似荒诞不经的涂鸦,透过波洛克淋漓滴落着油彩的画笔,我朦胧记起旧日曾有些似懂非懂的文字,于是重新拿起诗集,像是抓住了儿时即已失去联系的亲人的臂膀。夜深人静,我常觉得无比的幸运。
诗人都会死去,如永恒轮回。如果我为他们的谢幕流下几滴伤感的泪或书写几句廉价的缅怀,那将是对诗人的大不敬。诗,永远不会过时,它是精神在呼吸。只要灵魂还会经受折磨,只要地上还有花开花落,只要天上星辰不灭,只要还有人愿意为爱和激情而活,诗的溪流就永远不会干涸。词语不只具有功能性,它更可以真实而充满美感,它是诗歌艺术唯一的介质。我们还能找到源自人类本能的、比词语更接近生命的介质吗?
中年老友相见,除了毫无新意的唏嘘,话题也都味同嚼醋,了无生趣;Dead Poets也只是店主从文艺片中借来的一个名字,酒吧里除了酒精,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与诗有关;至于这年月若想找人说话,弹指之间便有无数颗寂寞的心。所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秋夜。
那个夜晚已过去半个多月,上海进入了冬天。遇上没有阳光的日子,灰暗和阴冷会带给人莫名的忧郁,甚至寒到骨髓。望着窗外雾蒙蒙的天空,我想起不久前那个秋夜,只觉得有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让我不着边际地敲下这些半真半假的字。
2020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