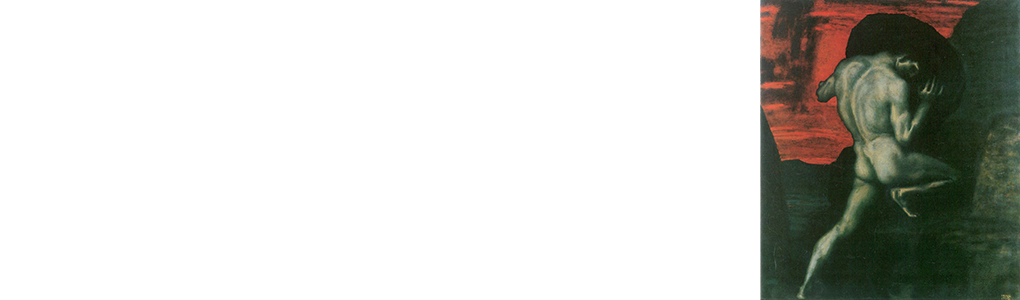如果有一天我能梦想成真出本书,那书的名字应该叫《呻吟集》,这是因为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是无病呻吟。我倒觉得,在各种声音中,可能只有呻吟才最真切、最原创。鲁迅曾经说:当沉默时,觉得充实;当说话时,觉得虚空。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当呻吟时,才觉得活着。
这几个月瞎忙,闲暇的时候我在编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姓费,有个英文名字叫菲利普,大家都叫他费离谱。故事发生于2019年9月的几天,老费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大学同学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老费毕业那年犯了严重错误,没有拿到毕业证。此后三十年中,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正式工作、没有买房购车,一直在城市里飘着,以做英文翻译维持生计。他从来没参加过以前的周年聚会,这一次回去,是因为他大学最好的朋友成了大企业家,要给母校一个巨额捐款,特意要他参加仪式,而他正好也想求同学办事,于是厚着脸皮前往。
这是我第一次编故事,用第一人称写七天的流水账,穿插着三十年里的很多回忆。三个月里写到第三天,已经八万多字,估计写完还需半年。这就是我为什么最近不能更新公众号。我不是为出版而写,能在公众号上连载也行。
有人说第一次写小说,基本上都是写自己。但我很靠谱,不是费离谱。我有一大堆毕业证,始终有正式工作,人生的规定动作都已按部就班地完成。此外,我比费离谱年纪大,他和我妹妹一样是85级。前段时间,我被拉回到早已退出的班级群,这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学要纪念八十年校庆,我们班也要搞个线上的怀念建班周年庆。热心的组织者说,视频聚会的主题是感恩、感动、怀旧、展望美好未来。届时,九十多岁的老系主任要致辞,当今的院长要讲话,当年的班主任要抒怀,老同学们都要发言。昔日全班三十一人,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自毕业就没有过音信,其余都在群里,全部聚齐。
我常怀疑带有“感”字的词汇,或许可以称为本能反“感”。在大家欢呼“凑齐”并开始发表感言之际,我再次决然退群。事后我自问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点抓马,我的朋友也问我是不是受到过伤害。其实,大学时代的班级是个以团结闻名的集体,处处充满积极、上进和嘘寒问暖。如果说当年我幼小脆弱的心灵受到过什么创伤,那主要是源自理工科大学女生太少,而我又实在没有竞争力。退群不参加聚会,完全是因为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感恩。努力了半辈子,走了不少弯路,我才勉强清掉读书时被他们灌进脑袋里的水,才让自己没成为他们希望我成为的人。我现在所信奉的,和当年被教导的,几乎全部背道而驰。如果我去感恩,则未免太过虚伪。
我的同学中,有人发大财,有人做大官,他们是学校的骄傲。对于他们的受瞩目,我没有丝毫妒嫉。像我这般次品,要想被注意到,唯一的方式是逃离,就像在大型团体操表演时突然溜掉。多少年来,人们总把“凑齐”当成目的,把步调一致看成美感,而将离群索居者视为异类。对此我不买账,我的不通人情只是一种姿态的开始:不用再去假装爱集体,无需再参与任何集体性的感动,可以拒绝表演团体操。或许,有一种存在就叫缺席,有一种诚实就叫忘恩负义。
最近离世的第一任007扮演者康纳利说,有意义的人生,多少都应该有点Anti-Social。反社会和反高潮(Anti-Climax),前者需要勇气,后者需要清醒。人们惯常所接受的词语、表情和形象中,充满Kitsch(刻奇),充满以多数为名的夹持。那是已经被讲过成千上万次的美,那是毫无新意的自我感动,是给丑陋世界戴上的漂亮面具,它意味着集体性撒谎的故作多情。毕加索说,艺术是谎言,但它揭示的是真相。揭示真相,意味着你自己必须能跳出来那个局,发出疑问,抽丝剥茧,冷酷地凝视周围的一切。在这一点上,我想到米兰-昆德拉。
萨比娜在《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是个画家,她一直与生活本身若即若离,并随时准备从所有自我感动的场景和关系中脱身而出,毫不妥协。生活在布拉格之春时代的捷克,作为一个美貌的女人,保持清醒谈何容易。但她是纯粹的:在反侵略的慷慨激昂中,她看到爱国热忱所需要的盲从;在情欲的迷乱中,她听出山盟海誓所隐含的占有。为此,她不得不带着那顶代表她“从哪里来”的圆礼帽,一次又一次地逃离。萨比娜也是幸运的:她有勇气去背叛传统、祖国、家庭、爱人,除了坚忍不拔的信念,她还有美貌和才华,她能逃离到瑞士和美国,那里的人们善良而又热爱艺术,愿意出钱买她的画作。
要么叛逆,要么油腻。这个道理,我年轻的时候并不懂,而是油腻到中年之后才慢慢明白,这就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读不懂毛姆的The Human Bondage (人的枷锁)。毛姆小说主角的名字也是菲利普,他从小到大有过很多梦想,很多追求,做过很多离谱的事,经历孽缘生死之后,才发现梦想和追求都是枷锁。用中国人的说法,这叫作茧自缚。
关于生命或者存在,昆德拉将其分成“轻“与”重“两种状态。毛姆所说的人的枷锁、我们提到的“茧”,如教条、责任、梦想、财富、名声、惯例,等等,无疑都属于人们背负的重担。而萨比娜追求的是自由、是真相,是一种“轻”。这种“轻”,是不可承受的轻,是另一种沉重,因为它意味着背叛终极才能感受得到的那种虚空。因此,对于萨比娜,在暮色苍茫中,她为幸福人家窗户中透出的柔和的光落泪;而那个与她的惺惺相惜的浪荡子托马斯,则抱紧了乡下姑娘特蕾莎。
也就是说,人们总有逃不掉的沉重,总会有落泪的一刻。“不管人们对刻奇有多么蔑视,它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为何所累,因何动情,是一种审美选择。
米兰-昆德拉这本《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我已经接触过三次,最近这次才算是才读懂。上次读是十几年前,翻了几页就放下,那时根本没这个心境。这次重读,我想起一件多年前的往事。
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课题组来自北大的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当时正在读哲学系博士的女孩子。这个来自南京、此前毕业于南大的女孩比我大两岁,已经结婚,爱人还在南京。她很好看,白皙清爽、聪慧而且沉静,至今我都记得她那双明亮的眼睛。那时,我很毛躁,但因善于给知识分子拍马屁,年纪轻轻就在一个很有影响的杂志社当特约编委。有一天,女孩递给我很厚很厚的一摞书稿,告诉我那是她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让我帮她问问有没有出版社愿意给她出版。
那厚厚的译稿,都是她工工整整亲笔誊写,每页四百个字。我抱着书稿找了出版社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这个作品的译文已经出版,书名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当时我怀中的译稿的封面上,有五个娟秀但有力量的字:沉重的轻浮。
我只好把译稿还给这位朋友,如今早已不记得当时和她见面的情况,但能想象她肯定会有的失望。不久之后,我出国做合作研究离开了北京,和这位朋友从此再没有联系过。在英国的时候,我很喜欢Daniel Day Lewis和Juliette Binoche主演的被翻译成《布拉格之恋》的改编电影,每次看这部电影都会想起那厚厚一摞《沉重的轻浮》。但只有最近这次重读,我才明白为什么昆德拉后来再也没有允许任何人去改编他的小说来拍电影。也只有最近这次读完,我才很想再能见到那位曾写下《沉重的轻浮》的女生。
20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