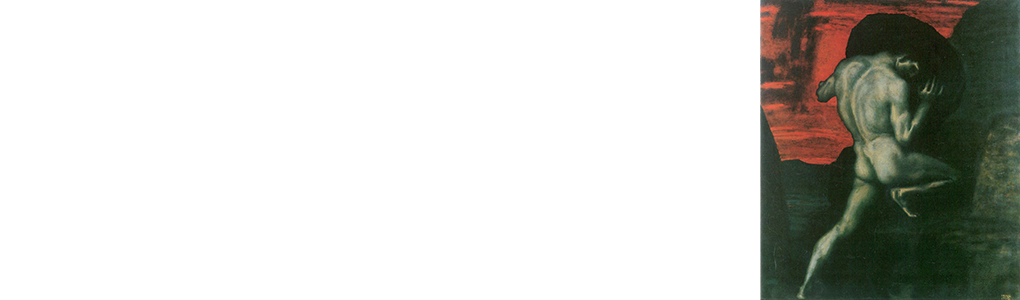自从十几年前搬来上海,我有很多时候是在咖啡馆工作的。
我喜欢的是那些宽敞、安静、有对着街道的窗户的咖啡馆。问题是,安静的咖啡馆一般是没有什么生意的。所以,这些年里,我去过的咖啡馆,大都坚持不了太久。每隔两三年,熟悉的咖啡馆,说不定哪一天突然就关门了,我只好再寻找新的。就这样,十几年也就晃里晃当过去了。
半年前在古北,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咖啡馆,上下两层,楼上面积很大,有靠窗的座位,可以看到窗外街道婆娑的树和斑驳的阳光。这个咖啡馆生意还不错,据说已经开了很多年。好处是靠窗的那些座位,被隔成了若干个比较小的空间,即使有时外面有些吵闹,坐在隔断的座位上做自己的事情,可以完全不受打扰。
我一般是午饭后到咖啡馆工作或看书,服务员和我都很熟了,知道我只喝美式咖啡,加一丢丢鲜奶。为了最大可能地支持咖啡馆的生意,我一般还会下午四点钟点第二杯咖啡的时候,加一块蛋糕或一个吞拿鱼三明治。
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这段光景,离我最近的四人座位上会来一些三十多岁的女性,有时是几个讲上海话的,有时候是讲台湾普通话的,有时候是韩国的,有时候是日本的。古北是个国际社区,这旁边有个幼儿园,她们是来接孩子的。
我一般不关注她们聊什么,即使关注,也听不懂。但慢慢我发现,不管是什么国家的,她们的笑声、讲话的表情和声音其实都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我甚至可以推测她们聊的基本上都是相似的内容。有时不仅会有小感慨:尽管东亚国家之间相互不服气,但这些国家里,婚姻生活对女性的摧残应该是差不多触目惊心的。
好莱坞的大导演大卫·林奇说:我看世界,荒诞无处不在。人们一直做着莫名其妙的事情,以至于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视而不见。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咖啡馆和公共场合——我的意思是,瞧啊,他们都在那儿。林奇在他的书里还说,在咖啡馆里思考,会更有安全感——你点一杯咖啡或者奶昔,让思绪去陌生而又黑暗的地方,而你最终总是可以回到咖啡馆的安全里。
在我熟悉的作家中,加缪是最喜欢描写咖啡馆的,他书里的很多故事都是在喧嚣、气味混杂、灯光昏暗的咖啡馆发生的。加缪对荒诞的理解,来自阿尔及尔小城咖啡馆里的人和气氛。我在巴黎的时候,曾经住在圣日耳曼大街(Saint-Germain-des-Pres) 的一个小酒店,离双叟咖啡馆和花神咖啡馆很近。这两家咖啡馆,是当年萨特、波伏娃和很多后来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经常光顾的地方,是存在主义的诞生地。100多年的历史了,依然存在着,生意更加兴隆。我没感觉到巴黎是海明威所讲的流动的盛宴,巴黎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永不打烊的咖啡馆。

傍晚六点左右这段时间,是我的咖啡馆最清静的时刻。人们都回家或去别的地方吃晚饭了,咖啡馆二楼经常就剩下寥寥几个孤单的人。这时,我会注意到,咖啡馆里的背景音乐好像从来不换,廉价的忧伤,听不出什么美感。而窗外,路灯亮起,天上,看不到一颗星星。
2018.10.28